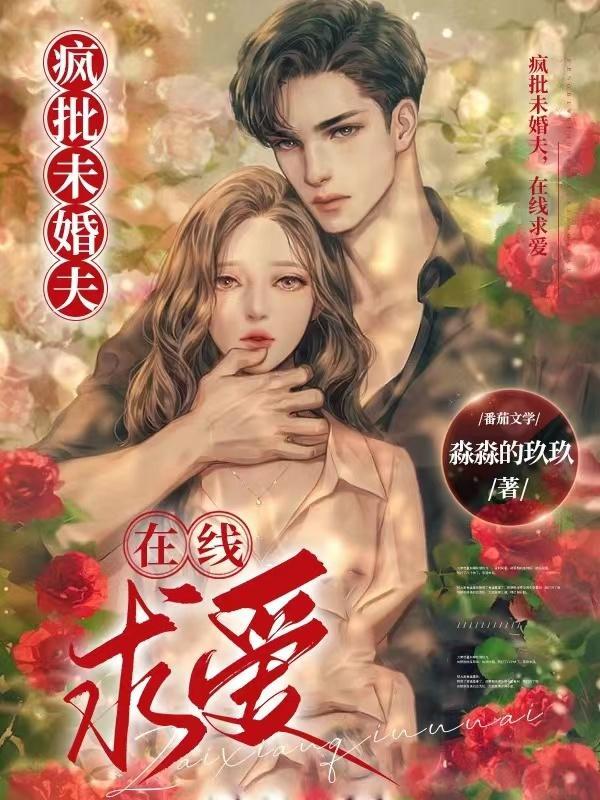风云小说>燃骨余三壶笔趣阁 > 第39章(第1页)
第39章(第1页)
这些还只是不相关的。更何况,谢氏偌大盛族,即便是帝王要做到缜密无瑕,也需多方协作。
于是,更有许多人,曾做了庆利帝手中的刀。
谢家二十一口,每一滴血,都有这些人的份。
他们怕谢燃报仇,不愿他活着,想斩草除根。
一年过去,谢燃在盛京酒楼,已无人敢作陪。
少年盛景尽散,繁华犹如一梦。
又是两年,谢燃二十生辰,及冠。
这是男子一生最重之礼,尤胜洞房花烛,金榜题名。
昔日谢明烛才名无双,高朋满座,出身贵胄,如今冠礼即将来临,竟无宾客宴席。
因为他的父母故长都死了,无人为他加冠。
“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谢燃舍弃明烛之字,枯坐一夜,晨起之时,为己束冠。
他就这样一日千里地走出了少年青年时光,不再偏爱明亮绚丽的事物,也不再爱热闹繁华喧奢侈。
他喝酒时也不再张扬地包上一层盛京最繁华的酒楼,再并上十艘画舫……而只是一个人坐在三楼窗边。
及冠当晚,谢燃点了几碟下酒菜,一壶酒,三个杯子。
他自己面前放了一杯,另两杯也盛满了,对面却并没有人。
谢燃将面前那酒一饮而尽,而后依次举起另两杯酒,倒于地面。
窗外依稀黄昏,摊贩归家,夫妇相携,小儿玩闹,一派烟火。
谢燃又为自己倒了一杯酒。
一杯又一杯。
他摇了摇酒壶,现已然空了,刚要唤小二,手腕却被一人握住了。
“老师……”阿浔的声音小心翼翼,却不由分说地握着他的手腕:“你不能再喝了。”
谢燃抬了下眼睛,曲指在少年的手上轻轻敲了下,道:“叫着老师倒管起我来,今年都十五了吧,别动手动脚的乱撒娇。”他声音淡的很,因此听的人也分不出这到底是恼怒,还是纵容。
自谢家灭门,三年过去,当时那些围着谢燃的人都跑了,竟然只留下这个名叫“阿浔”的少年。
少年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出现在他身边,又总唤他老师。
阿浔勤奋,又聪敏异常。于是时间久了,谢燃便真的教了他读书识字、骑射礼仪。
聪敏异常,谢燃渐渐也把隔日的授课当做一桩解压闲事。
少年家贫,没有金,便在课后为谢燃做一餐饭,饭后陪谢燃下一局棋。
日以继日,竟不知不觉成了习惯。
他们竟然就这么相伴过了四年。只是少年从来看不清谢燃的心思和真实想法。
谢燃变得总是淡淡的,曾经那明亮的少年似乎早已死在了这具精美华贵的躯壳里,像火燃后的灰烬。
他似乎无可也无不可,即使每天都风雨无阻地来这里吃一顿饭,下一局棋,但没人看得出他有多留恋。
就像没人知道,他到底爱什么,还关心什么,又对何人有所眷恋。
他藏的太滴水不漏,连对方,甚至连他自己……或许都意识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