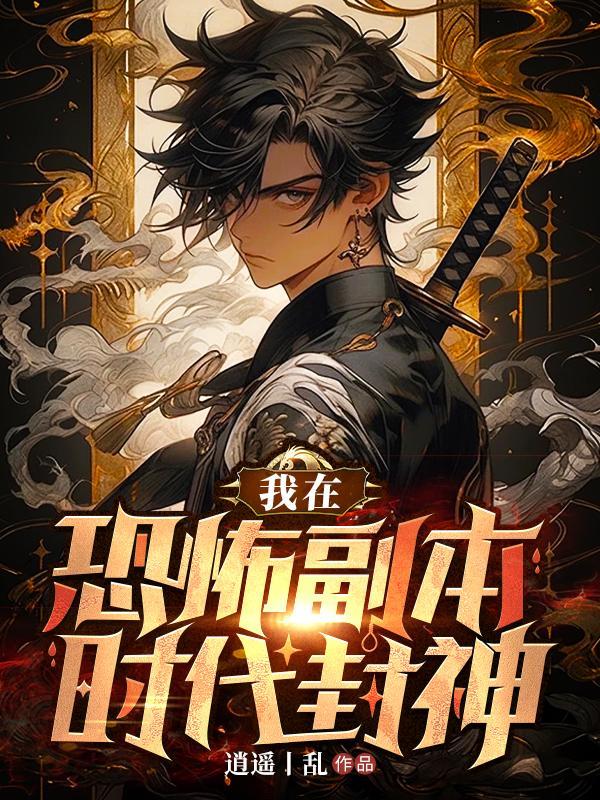风云小说>人间失守秦放的结局 > 第三十八章(第3页)
第三十八章(第3页)
邢朗严声道:“先不讨论你的儿子是什么样子,现在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只要你配合,回答完问题就可以带着你的儿子离开;如果你不配合,公安机关有权利扣留你们满四十八小时,甚至可以以妨害公务罪拘留你,”邢朗看了一眼还在发呆的陈雨,“还有你的儿子。”
何秀霞眼中涌出忌惮,既气愤又无奈道:“怎么能,怎么能抓我们……”
邢朗沉着脸对何秀霞说:“我们有执法权,女士。”
然后,他给了魏恒一个眼神,示意魏恒可以随时开始。
魏恒调整了一番坐姿,把桌子上的两个证物袋推到陈雨面前,叫了一声陈雨的名字。
陈雨听到有人唤他,循着声源看向魏恒。
魏恒放柔了声音,尽量不给他造成任何压力,看着他的眼睛轻声问:“看看这两样东西,你见过吗?”
两个透明的证物袋里,一个装着一只普通的红底白花的发夹,一个装着一块红色塑料纸制作的风车残片。发卡是当年郭雨薇失踪后,警方调查走访时从陈雨卧室中搜出来的。而风车残片则是死者白晓竹紧握在手中的唯一物证。
现在魏恒把这两个物证拿出来,试图刺激陈雨,逼迫他做出一些反应。让他失望的是,陈雨看到发卡和风车碎片并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陈雨本就呆滞的目光落在两只证物袋上时只是变得更加浑浊,更加迷茫。
魏恒观察着陈雨的神色,正欲进一步诱引他开口时,忽听何秀霞哇哇叫道:“你不要问他!他的脑子坏掉了!”
陈雨被母亲突如其来的嚎叫吓了一跳,眼睛里浮现些许惊恐之色,然后痛苦地捂住耳朵,低下了头,像一只把头扎在沙地中的鸵鸟。
邢朗皱了皱眉,曲起食指叩了叩桌子,音量不高却十分威严:“坐下。”
何秀霞忌惮他,一边忧心忡忡地盯着魏恒一边慢慢坐下。她看待魏恒的眼神充满了敌意,魏恒在她的眼神中看到了徐苏苏的母亲刘淑萍的影子。她们同样都是疯狂的母亲,只是她们疯狂的源头大不相同,刘淑萍是丈夫的异教徒,而何秀霞是儿子的保护神。
陈雨受到惊吓,一时半刻无法接受问话。魏恒索性向何秀霞提问:“那你来回答,十月二十一号,昨天晚上六点到九点钟,你的儿子在哪里?”
何秀霞两只凹陷的眼睛瞪得尤其的大,盯着魏恒一刻不敢放松:“他在店里,和我在一起。”
“你店里有摄像头吗?”
“有。”何秀霞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连忙补充,“他在后面仓库里睡觉,仓库里没有摄像头。”
魏恒既无奈又觉得好笑,何秀霞虽然战斗力强悍,但是她显然不是聪明的人。不过退一步来讲,就算何秀霞迫不及待爆出底牌,只要警方找不到证据推翻她的证词,就无法证实她说谎。
魏恒拿起装有风车残片的证物袋,举到她面前:“知道这是我们在哪里发现的吗?”
何秀霞摇头。
魏恒看着她那双露出些许凶意的眼睛,道:“一个女孩儿的尸体身上,她被人活活勒死,然后被丢弃在金鑫玻璃厂的旧仓库里,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六点到九点之间,如果你不能为你儿子提供有效的不在场证明,我们就可以拿着搜查令搜查你们的家,直到找到这个风车的另一部分。”
对于审问技巧,何秀霞一概不知,她也不懂得如何避让,如何拆招,她只是基于心底对儿子的保护欲,迫使自己的大脑做出防御。
她跳起来,粗俗又野蛮地叫道:“你们不讲理!我们家里卖的就有这种风车,难道我们家有这种风车,人就是我儿子杀的吗?!你们警察不可以这样办事!我儿子是傻子,但是你们不能因为他是傻子就欺负他!你们和那些欺负我们娘俩的人没什么两样!”
邢朗问道:“欺负你们?谁欺负你们?”
何秀霞陡然变得激动起来,她粗鲁地把陈雨捂住脑袋的双手掰开,拉开陈雨的运动服外套,捋高陈雨的袖子,露出零散分布的伤痕:“你们看看,这些伤,全都是那些狗杂种给他打的!”
魏恒略扫了一眼,就看出那些伤是木棍抽打出来的伤痕,皮下出血严重,表面大面积挫裂,甚至有可能造成了骨骼损伤,可见打他的人下手多么毒辣。
魏恒心里猛地一沉,问:“什么人干的?”
何秀霞抹掉脸上的泪,又帮儿子把衣服穿好,狠狠道:“郭雨薇那家人,他们差点把我儿子打死!”
邢朗懒懒地抵着额角,并没有因为陈雨身上这点伤就对他产生同情,语气一如平常道:“为什么?”
何秀霞眼睛一闪,抿住嘴巴不说了。
邢朗道:“如果你不配合,我们就找郭雨薇的家人。”
何秀霞似乎意识到自己的隐瞒没有一点用,搓着双手垂下脑袋,低声道:“几天前,郭雨薇的生日到了,我儿子拿了一个风车放在他们家门口,但是被郭雨薇的爸爸发现了。然后,他们就把我儿子拖进他们家里,打了个半死。”
回忆起那天,何秀霞浑身发抖,眼泪不停地流,用力搓揉粗糙的手掌,发出类似枯萎的老树被撕掉树皮的声响。
被施暴的受害者陈雨此时依旧看着窗外发呆,双手插在双腿之间,像个不倒翁似的前后摇晃。
魏恒看着面容呆滞眼神空洞的陈雨,忽然想起了张东晨,想起张东晨家中浓重的中药味,被砸碎的阳台玻璃,还有被剪掉半只耳朵的小虎。
不知从哪儿来的默契,魏恒转头看向邢朗,发现邢朗也在看着他。虽然他们没有交流,但是魏恒看得懂邢朗眼神中的含义。
邢朗对他说:结束吧。
陈雨被母亲牵着手走出魏恒的办公室时忽然在门口止步,他回过头,原本浑浊的目光忽然变得清亮,如大梦初醒般看着邢朗发了一会儿怔,然后咧着嘴挤出僵硬的笑,道:“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