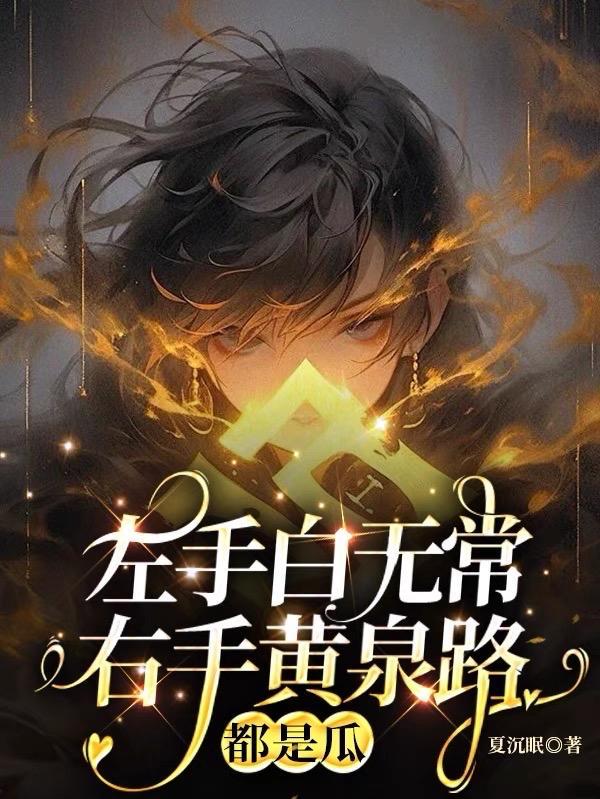风云小说>那个多情的四少爷免费阅读 > 六十九我的囡囡受苦了(第1页)
六十九我的囡囡受苦了(第1页)
苏慕北慌乱地收拾了一个包裹,奔赴车站,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火车行驶了十二个小时,苏慕北下了车,在站台上四顾,暮se四合,心中寥落,不知该去往哪里。
问了一同下车的人村子方向,苏慕北走到村头已是暮se西沉。想是刚落完雨,田间小路泥泞不堪,行走艰难。
一声啾鸣,水田里窜起个黑影,苏慕北脚下一歪,踩进泥坑。苏慕北惊魂未定,抓紧手中的包裹,咬着牙跑过水田。
村头亮着灯,是打谷场上头新拉的白炽灯泡,明晃晃的,却照不远。
苏慕北循着记忆来到一户农家,抬手敲了敲门。隔壁院子里传来狗叫,苏慕北一惊,心在x口扑通直跳。
门里传来声音,问:“谁啊?”
苏慕北辅一听见,泪就落了下来,用手背擦拭g净,声音发紧:“阿婆,我是慕北。”
木门从里面打开,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太,手里提着盏油灯,眯着眼睛朝苏慕北脸上打量。
苏慕北往前一步,叫了声:“阿婆。”
阿婆皱着的眉头松开,满是褶皱的脸上绽开笑容:“真的是囡囡。”
阿婆握住苏慕北的手,把她往屋里带:“老婆子以为自己在做梦,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囡囡还会回来。”
阿婆的手g燥温暖,苏慕北因为连日奔波而仓皇疲惫的心在这一刻奇妙的安定下来。阿婆手中的油灯仿佛是她生命中久寻不到的灯塔,让她不再彷徨。
“阿婆,”苏慕北咬唇,“是我不好,这些年也没来看过您。”
阿婆把油灯放到木桌上,在灯光下仔细打量苏慕北:“大了,b小时候更加水灵了。”
她笑着,眼睛中没有一丝责备。
苏慕北道:“以后我就不走了,在这里陪着您,伺候您。”
阿婆笑道:“老婆子不需要人伺候。倒是囡囡,需要人来疼的。”
苏慕北想起谢长安,心揪着疼,声音就有些发颤:“没有人疼囡囡,囡囡只有自己。现在有了阿婆,囡囡觉得不再孤单了。”
阿婆摇了摇头:“我家囡囡那么漂亮,x格又好,怎么会没有人疼。”
苏慕北心中的痛苦再也止不住,扑进阿婆怀里,哭道:“阿婆,我好难过。”
阿婆拍着苏慕北的后背,心疼道:“怎么了,怎么了?囡囡在外面受苦了,我的乖囡囡。”
苏慕北ch0u噎着说出了与谢长安的一段过往,从两人相识相知到相厌相离,说谢长安如何不专,如何绝情,说谢府对自己如何淡漠,对谢长安又是如何纵容,说人情冷暖,各种苦辛,所有的不甘,所有的谴责,都对阿婆说了出来。
阿婆的怀抱很温暖,阿婆的眼神很慈ai,她静静的听着苏慕北的诉说,虽然不曾说话,但却让苏慕北觉得她是这世上唯一一个懂自己的人,也是唯一一个不会拿自己的悲惨经历耻笑自己的人。
在阿婆温柔的眼神中,苏慕北愿意揭开自己所有的伤疤,哭的畅快淋漓。
“阿婆,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这些日子我简直要疯了。”
阿婆叹道:“时间会让日子好过的。”
苏慕北问:“阿婆,他为什么这样对我?”
阿婆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x格,孩子,他那样对你,你是不是也有过错呢?”
苏慕北想了想,摇头:“没有。”
阿婆笑了笑,说:“那就是他不懂得珍惜。”
苏慕北心中好受了些,仍旧腻在阿婆怀里不愿意起来。阿婆宠溺地帮她理顺鬓边散落的发丝,擦掉腮边泪水。
“留下吧,囡囡,等心里的伤好了再离开。”
“我会一直留在这里,永远都不会离开了。”苏慕北x1了x1鼻子。
阿婆摇头:“这里不属于囡囡,囡囡还是要走的。”
“我不管,”苏慕北抱紧阿婆,“我现在只有阿婆了。”
阿婆叹了口气:“我的囡囡受苦了……”
苏慕北小时失怙,是阿婆捡到襁褓中的她,当亲生nv儿抚养。后来在苏慕北五岁的那年,赵家老爷带小nv儿游历经过村庄,看中了长相清丽的苏慕北,便提出要收她做养nv,陪赵晓清一起去北平读书。
阿婆当时问苏慕北要不要跟赵老爷去北平,小小的苏慕北看着赵晓清身上的白se蕾丝边儿公主裙,点了点头。
阿婆是为苏慕北有机会去北平而高兴的,他们所在的村子太小,太闭塞,苏慕北如果待在这里,一辈子都看不到外面的世界。阿婆希望苏慕北活得开心,自由。
时隔多年,苏慕北再次回到了这里,阿婆已经老了,原本的满头青丝变作白发,年轻时饱满的脸颊也凹陷下去。但亲情还在,那种血缘之外的完全靠人与人之间的善心构建起来的亲情更显得珍贵。
回到乡下的。我问他什么章,他说是老爷定下的规矩,所有财务调度都必须要有印章。”
杜晓清淡淡望向谢长安,脸上现出俏皮神se:“老爷大人,到底是什么章,可否让小nv子见识一二?”
谢长安想了半晌才明白过来,拍了下额头,道:“竟然忘了这事。明日我便去找那管事,废了这项规定。”
杜晓清点头,也没多说什么。
谢长安早已丢失,夫人可随意支取银两,不需额外的琐事规定。
管事道:“既然是老爷的规定,我们没有不遵守的。”
本以为这事便这样平息了,谁知晚间温柔缱绻时,杜晓清又提起此事。
“我见往日的支票清单上确实是有印章,那印章倒也别致,刻的是什么‘北暮长安’,是你与苏慕北的名字吧。”
谢长安在卖力冲刺,正在兴头,没怎么理会她的话,只淡淡的“嗯”了声。
![职业反派[快穿]](/img/1860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