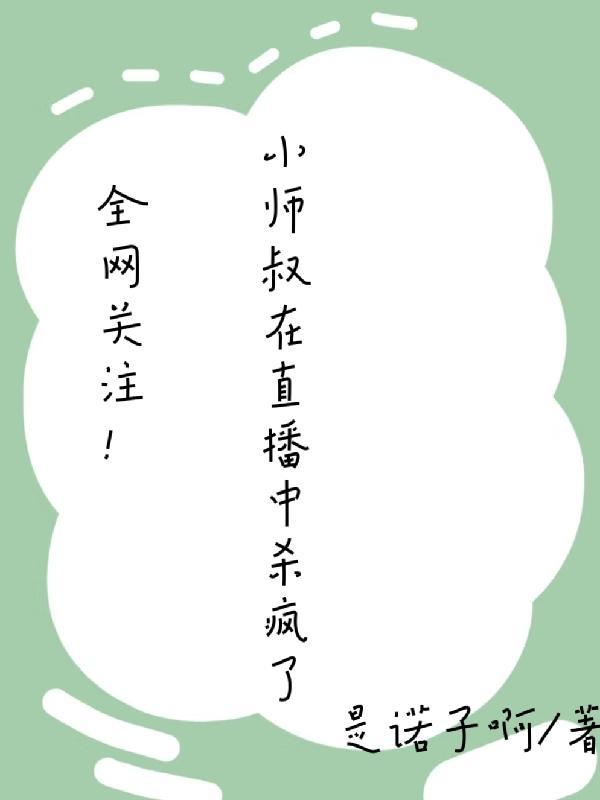风云小说>大明女医纪事乔小懒懒免费阅读 > 第63章(第1页)
第63章(第1页)
“老?夫要听你说。”
她方开了口,缓道:“此疏所?陈国之积弊,乃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皆出于血气壅阏,而这尽源于当今圣上怠政,故此上书劝谏其?广开贤路,励精图治,方能解朝局之困。”
“你倒是第一遍就能读出意味来。”徐阶也不知是否嘲讽。
顾清稚不敢答话,耳旁听得他道:“此《论?时政疏》乃当年太岳登奏,亦是迄今为止最末一道,主上并未视过,送入内阁来时老?夫见了大骇,可谓直指圣上之过,老?夫深恐此等锋芒毕露之谏言为人所?惮,生?生?将其?按下不表,保他内抱不群而能安然居于这朝堂。”
她动容:“如此……真是为难外公爱才之心了。”
徐阶又视她:“你当真知晓他是何等人?”
“我知之不多。”顾清稚与他目光相对,“但我愿意陪他成?为他所?期望成?为之人。”
徐阶展唇:“好志气。”
他续道:“老?夫观其?人身负国器,此后必居于诸人之上,比之老?夫乃至严阁老?,甚或本朝开国以来诸位宰辅皆愈有改天?换日?之气量,然这权柄在握,脊背必是棘刺满身,稍有不慎,即是全?盘皆输,再无翻转余地。你可有预知此后种种险阻困苦,尽须由?你撑起?”
顾清稚点头?。
徐阶沉静端详她眼眉,想这外孙女此前善会察言观色,少有这般坚定时刻,心下黯然,一时不知究竟是何滋味。
“那日?后若逢满朝攻讦弹劾,至穷途末路之时,你是悔还是不悔?”
顾清稚笑道:“这有甚好悔。”
门?外俟了半日?的张氏早已按捺不住,立时推门?而入,趋近了扶住清稚双肩:“莫听你外祖父胡说,哪能这般严重?你张先生?为人最是知进退有城府,又有这般雅量,听闻裕王府满门?上下没?有不喜欢他的,更不是那等执拗暴戾之人,谈何险阻艰难?”
“外祖母放心,这也就是外公提点我呢,不过是假设而已,哪里会真能如此。”
听她宽慰罢,张氏道:“你也坐下歇歇罢,夫君也真是,一日?到?晚便让小辈跪着听你教训,次辅大人的威风做甚么要冲着小辈发。”
徐阶不理她,终是撩袍往正位上坐了,看着顾清稚亦寻得一杌子休憩,便道:“老?夫方才所?言,也不过是给你事先提个醒,好教你谨慎思量这桩婚事。老?夫再问你一遍,你可是真心愿嫁?”
张氏亦探询视她。
顾清稚眸光凝于一处,语气毫无半分犹豫:“确是真心。”
“若是老?夫不肯呢?”
徐阶悠长目光投来,令她后背一凛。
“外祖父为何……”
“凭老?夫不愿让你涉险。”徐阶直截了当道,“老?夫恩师夏言阁老?一朝身死,可怜其?妻苏夫人年老?流放,命在旦夕,教人如何不为之心惧?”
张氏一听,顿时也失了镇定,丈夫话意她如何不懂,对着顾清稚的面上难免覆了愁苦:“你外祖父是怕你嫁了个有凌云抱负的,必定不甘心屈居下僚,日?后即便登上云端,我们也不愿看着自家掌间明珠承担那跌落尘土的后果,若是有性命之忧……那我见了也是不活了,你外祖父的苦心你可懂么?”
“我都明白?。”顾清稚始终未垂下眼眸,目光t?平视,“二老?不用为我挂心,你们尽管宽心,外孙女都晓得,也知该如何做方对得起你们这颗心。”
“你执意如此,外祖母必定支持。”张氏眼中担忧未褪,“你自小聪慧,万事不必我这个老?妪多言,只是……”
“你也莫说了。”徐阶打?断她言语,随即步出门?外,“来日?收了聘礼缔罢婚书,你便操持七娘出阁罢。”
窗格之外,冒着雪目睹屋内情形的徐元颢虽是能视,苦于风大听不清楚,那三人言谈愣是没?领会半个字。
“你在这做甚么呢?”张氏路过,睨他。
徐元颢忙后退:“孙儿在看……看光景。”
“还不快收拾去?”
“是。”徐元颢乖乖告辞,骤然闻得身后一声晴天?霹雳:“这回你一个人去罢,我派个知根底的小厮伴着你,一路小心,莫要让祖母牵挂。”
徐元颢不解:“怎么,七娘不走了么?”
张氏不答。
“张大人既已拟定婚约,这嘉靖年间进士登科录上的户籍事项可得修改了。”礼部侍郎笑道,取来一卷档册递予他。
张居正接过,挽袖蘸墨,于自己名字的那一侧家眷列里,端正楷体落笔:“妻顾氏。”
写罢,他停手?搁笔,阖上档册,随后下值出门?。
小雪纷飞而至,他行?至柳泉居楼外时,心中挂念着与顾清稚之约,脚步不由?得加快。
有一行?官僚女儿坐轿路过,瞧见雪中有一蓝袍官服男子等候于鹤年堂之畔,长身玉立,湛然若冰,不禁撩帘望去。
“好俊的郎君。”有女子赞道,“这官服穿他身上愈发夺目,倒像是浑然天?成?一般。”
“也不知是在等哪位姑娘,有这般颜容出众的相公,好生?福气。”
“我倒觉得是在候着哪位同僚,瞧他才下值就等人,怕是有甚么要紧事。”
众人议论?之间,顾清稚方乘着马车而至,远远地就见那男子伫立于檐下,雪色一径里白?茫茫铺开去。
“快停车!”她眼中有如闪过星子,连忙吩咐马夫,车停稳后立即奔下去,于众目之中小跑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