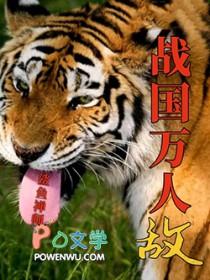风云小说>织魂引 百度 > 第245章(第1页)
第245章(第1页)
寅月神情坦荡,她就是故意的,而且连日来受的气都在此刻集中爆发,看见他因嫉妒而阴沉到极点的样子,她终于快意地舒了口气。
既然她不开心了,那就说点儿难听的出来让他也难受难受吧,来互相伤害。
李时胤勃然大怒,钳制住她的手松了又紧,“什么做了?什么时候?”
寅月想了一下,正准备要说,下一秒,所有话音都被他捂在掌心里,他的手微微颤抖,像是一个字都不敢再听,听完就要七窍流血。
李时胤捂住她的唇,将她死死抱在胸口,满脑子都想着把帝胤这个趁人之危的畜生除之而后快,他不过和她别扭几日,他就将她勾引了去,竟让他们在眼皮子底下谈婚论嫁了?
他们究竟做什么了?
寅月任他抱着,没有反抗,模糊的声音还是传进了李时胤耳朵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春宵一刻,红被翻浪,你我做得,我和别人就做不得?迟早要做。”
箍紧她的双臂明显一窒,继而飞速收紧,像是要勒碎她,肩头一沉,是他的下巴落在了她肩上。仿佛他在捧着最脆弱的宝物,只有抱得紧紧的才不会在怀里流失。
“我为你连命都不要,他呢?他能为你做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心疼心疼我。”
他滚烫的吐息落在她脖颈耳侧,柔软的嘴唇贴在她的皮肤上,寅月一下心软了一截,底气不足了,“你能做的多了去了,你不是一样可以和旁人谈情说爱谈婚论嫁。”
李时胤伏在她肩上,闻言松开她,严肃又茫然盯着她的脸,“我?和谁谈情说爱。”
寅月移开视线,打心眼里认为这样拈酸吃醋很难堪,不体面。
原来是在吃醋?
这点儿介意让他莫名雀跃了一下,李时胤心念电转,一下找到了症结所在,“你说妖都酋山一族的狐女?她与新晋的凤凰山山神是一对,因门第之见,她家里不同意,我帮着谋划了好一阵才成事,还替他们请了吉服,上头还有你的神力加持。”
他随手划了一道,眼前现出一张烫金喜帖,工工整整上书着那二人成婚的日子地点云云。
那针刺一样的情绪倏然消散了,寅月竟不知道表什么情,“你故意怠慢我是真,白溪说那些难道有假?”
李时胤捏捏她的脸,又气又好笑,又束手无策,“他懂个屁,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听个戏文都能认为哮天犬和二郎神是一对。我只是和你赌气,你做什么了?”
赌气又能如何?
到头来伤心的还不是他自己,他赢不了她的,因为她没那么爱,可他是一颗真心明明白白要全部奉送给她的。
她说,“我也一样。”
李时胤捧起她的脸,目光灼灼,“我只想问你两件事,你如实作答。”
当初活过来,李时胤以为第一眼可以见到她,可是没有,再等也没有,又想到往日种种,与其说是失望,不如说他是畏惧怯懦了。
他为她赴死,对她来说既是莫大的恩情,也是绑架,他不需要她只是带着报恩的心态,用那点儿似情非情的爱意和他在一起。
他知道,她没有非他不可,她没能像他爱她一样爱他。他有多喜欢,就有多容易失望,如果她的目光有一天会停留在别人身上,他能接受这种分心吗?
不能。
如果她不喜欢他了,他该怎么办呢?
所以,他不要一点儿,他想要她确凿无疑,要她绝无二心,要她坚定不移。
他期盼她迫不及待来找他,最好见面就扑过来抱紧他,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她有多喜欢他,多想他,要和他永远在一起。他立刻就会抱住她,把缺失的这些日子都补起来。
可是没有。
这些话如果不是她自己心甘情愿说出来,而是由他去要求,那就是挟恩图报,结果也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克制着,没去主动找她,而是在家里等。
她是来了,也不现身,来了还想走,他患得患失,越想越气越气越口不择言,所以对她说了气话。
第二天她也来了,可是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甚至不对他笑了。
他想,她只要多和他说几句软话,哪怕一句,哄哄他,他这么久的等待心酸,这么多无处宣泄的想念,他就全部原谅了。
可是也没有。
那日过上巳节,她临时带着厨子来做烧尾宴,他心里多甜蜜,他想她应该是把他放在心上的,所以郡主给他使眼色提醒他。
可宴会不能推掉,因为当日是那二人议亲的关键日子,他们为此努力很久,他一整天都心不在焉,心里盼她能等他,可又怕她等久了受挫。
终于把婚事说定了,他急急忙忙赶回去,人已经走了。
然后就再也没回来。
他左等右等,不去找她的决心开始动摇,没过几天,他还是藉着吉服的幌子,每日去织造署想看看她,不管讲不讲话,看她一眼就可以。
她的女官总说她在忙在忙,永远在忙,他猜应该是在推脱,她就是不想见不喜欢了。他想问问清楚,却总是见不上面,他能感觉她在躲他。
两人阴差阳错,今日才算正式把话说开。
寅月道:“哪两件事?”
“你对帝胤,到底是什么心思,你们之间……”剩下的话他都讲不下去。
“什么也没有,”寅月如实作答,“就是同僚之谊。”
李时胤的目光审视,“我和他比谁好看?”
“你和他不是长得一样吗?”
“那你说谁好看。”
“你。”
“我和他长得一样,你说我好看?焉知你不是在见人说人话,故意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