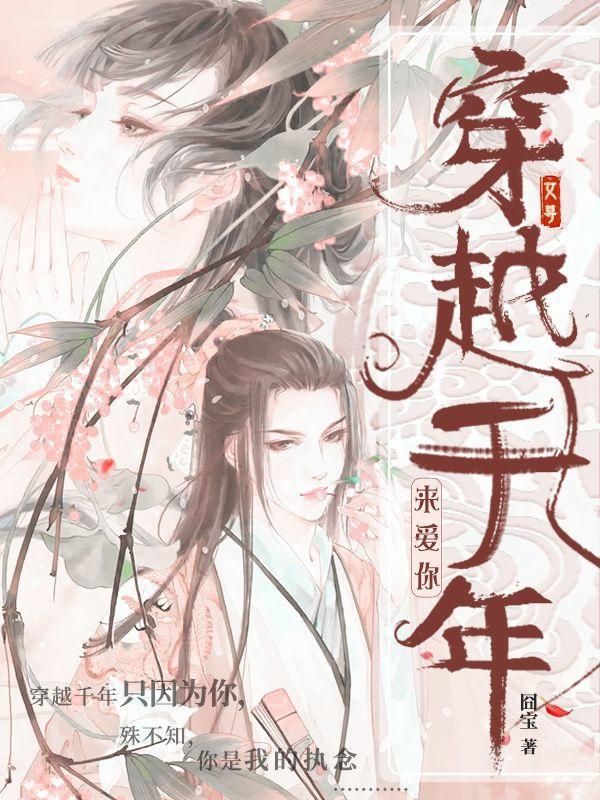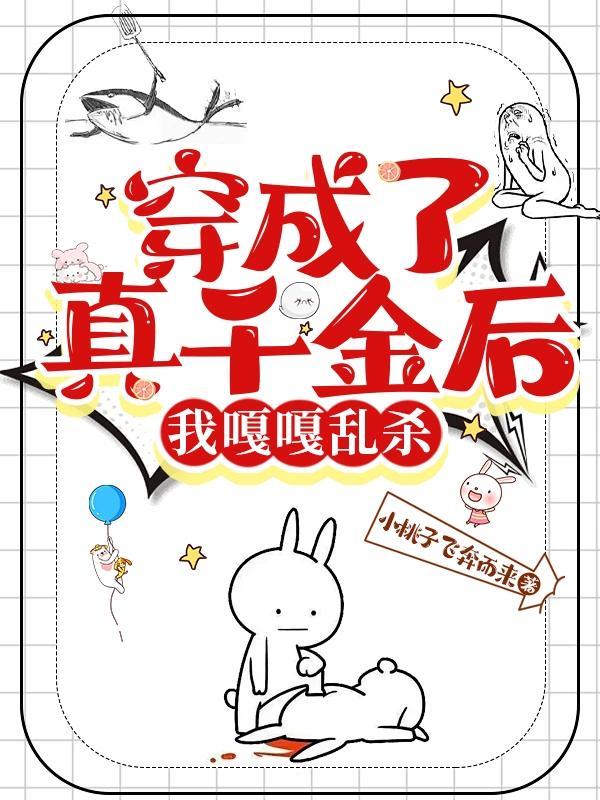风云小说>华年的解释 > 第13章 卷一 梦中的王子(第2页)
第13章 卷一 梦中的王子(第2页)
乐宝和杰克的恋爱,如果算一场恋爱,从开始到结束,一共正好六十六天。
乐宝与方鸿之认识一个月后,帮华年交了半年的房租,搬走了。
搬家的前几天,华年见到了她的新男朋友方鸿之。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标准的斯文俊秀。只是没有未然好看,那个时候的华年还记得未然的样子。乐宝笑呵呵地说,真是穷讲究,眼镜框也要买普拉达的。
乐宝提议一起去吃饭,方鸿之说好。他们去了在离华年打工鞋店两个路口的那家西餐厅。华年以前和乐宝总是经过这里,却从来没有进去过,当然是因为觉得贵。其实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餐厅,不过是一家全国连锁的牛扒店,牛扒是用劣等肉渣拼起来的,一个套餐加汤加沙拉加甜点大约一件H&MT恤的价格。她们小城里以前其实也开过这么一家,刚开的时候骗了小城里好多人。那个时候,洋玩意特别吃香,牛肉渣做的肉饼只要给取名某某牛排,就会立刻大热。开始华年和乐宝经常排队去吃。后来有一天,却突然的,就不流行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倒了闭。当初华年和乐宝发现上海竟然还开着好多家这个连锁店时,吃了一惊。其实,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便是上海,小气起来比谁都小气,包容起比谁都包容。
每次华年和乐宝经过这个店的时候,华年都会特别感慨,以前吃鲍鱼嫌腥吃熊掌怕胖,现在居然对着个肉渣饼流口水。
路上他们经过路边一个卖石榴的担子。乐宝说想吃。方鸿之就与挑着那担子的老农民讨价还价。老农只穿了一件单衣,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又特别干瘦,那担子在他肩上,看着有一千斤重,压得他直不起腰。
华年笑着说:“不还了,不还了。”
方鸿之说:“你不知道,我妈从小和我说这些路边摊的人最可恶,向来缺斤短两的,再不还价,要吃大亏了。”
华年和方鸿之初次见面,也不好再说什么。
他们三个人走到了餐厅,方鸿之问服务员特别要了个窗口位坐下,说要看着风景吃饭。
看得出,方鸿之很爱说笑话,一顿饭他都在说笑话。美国留学时学校篮球队的笑话,美国吃饭给服务员小费的笑话,美国半夜街上买黑酒喝的笑话。他说的话,一句要夹三个英语单词,是漂亮极了的纽约腔,和他晒得均匀发亮的小麦色皮肤一样漂亮,和他的棕色薄开司米毛衣一样漂亮。华年和乐宝练了那么久的英语倒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方鸿之的笑话每次还没有讲完,乐宝便开始笑,有时候笑得停不下来。到最后,华年只好跟着她一起笑。但很快华年真心地笑了,乐宝是真的喜欢方鸿之,这个男人迷住了她。
“我爸是个握手术刀的,我妈在四大会计事务所。我进四大,多亏了我妈老上司帮忙。”方鸿之说。
“他忙得很。”乐宝看着他笑。华年也笑。
那天华年吃得很饱,也没有再担心最后的买单问题,乐宝笑眯眯地看着方鸿之掏出钱包买了单,又笑眯眯看着他给服务员塞了五十元小费。乐宝悄悄给华年发了个消息,“男人果然还是买单的时候最有魅力。”
华年拱手给她道喜。方鸿之简直是梦中的王子,是专门为苦难女主角设的救赎,是黎明前破晓的那束晨光。
乐宝搬家那天,华年帮她整理行李,她带她去看她的新房子。乐宝的新房子和方鸿之家很近,还是个一室一厅的酒店式公寓,足足要了她半个月工资。华年打量了下乐宝的新家,房子装修家具上倒没什么,却在窗帘沙发床罩子上下足了工夫,一式的深深浅浅的带着珠串子的蓝色天鹅绒。华年看得出,这是乐宝能尽的所有力气。这浅蓝是方鸿之最喜欢的颜色。乐宝说还要买了个大平板电视机把这房东的小彩电换掉,倒是可以去二手市场逛逛,又问华年要不要再装个卫星电视,方鸿之平日里时刻要看BBC新闻。
“他要看国外的新闻,没个卫星电视不行。”乐宝说。
“国外新闻可以电脑上翻墙出去看,卫星电视贵,又不稳定。”华年建议。
“不行,鸿之在家里看惯了卫星电视,来这里每次还要翻墙出去看多不方便。”乐宝说。
“方鸿之的爸爸妈妈倒是开明,听说卫星电视可以随便看那种片子。”华年坏笑。
乐宝脸一红,“他还在美国读书时,他爸爸妈妈就给他买了新房子,三个房间呢,现在就给他一个人住着。”
“同人不同命,可惜咱家的金勺子弯了。”华年叹息。
“是啊,哪里有他这么好命的人?生得好又长得好的。”乐宝也叹息。
“我是说你!哪里有你这么好命的,找了男朋友生得好又长得好的。”华年笑。
乐宝搬走以后,周末不再出去玩,她经常会在周末的时候回来看华年。明明白天在一起工作的,可自从她搬家以后,还是觉得好像每天看不到似的。好长一段时间,华年都没有再看到过方鸿之。乐宝说他很忙,在这样的跨国企业里工作,平日里加班出差是家常便饭,周末还有兄弟聚会各种应酬。
“他这个洋鬼子,说周末是一定要和兄弟们出去喝一杯的。”乐宝说。
“这是哪门子规矩?”华年问
“你可不知道,他说这是华尔街的规矩。”乐宝回答。
“正经有这样的规矩?”华年不信。
乐宝说:“真真有的。Workhard,layhard,他天天挂在嘴巴。他们那个行业都这样。他说他们还是好的,四大服务的那些风险投资机构的人玩得才厉害,周末专门要包架飞机飞海岛的。”
“我不信。”华年说。
“我信。”乐宝笑。
“每个周末消失的男朋友和传销集团一个性质。”华年说。
“你以前没听薇薇安说都市男女的交往自然有都市男女交往的规则,不多问不多想不多爱。”乐宝说。
华年叹了口气,问:“风险投资是做什么的?”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方鸿之说他们是投行,和投资虽然只差一个字,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我再问,他就说,和你说了也不会懂,每次这样,我便要打他。”乐宝说着嘻嘻笑起来。
乐宝的这个笑容是华年记忆以来她最甜的笑容,比小时候看到漫画里最动人的情节时的笑容还要甜,是五月的蜜浆酒,酥麻麻地醉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