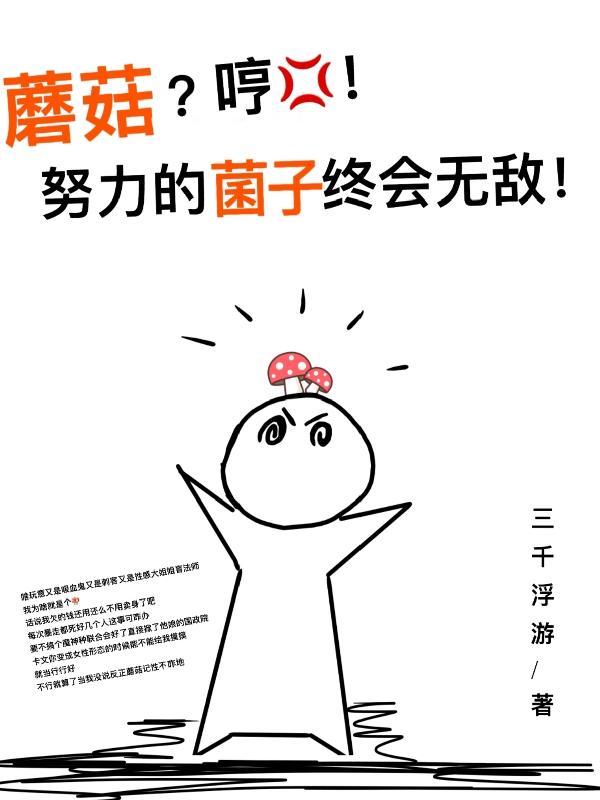风云小说>娇藏锦鲤半两无眠 > 第23页(第1页)
第23页(第1页)
“是吗?那佟大人,今晚就辛苦您了。”辽王妃微微颔首,阴冷的目光这才向臣寻扫过来,好似此刻才发现院子的主人在当场。
“应该的。以后要再有事,王妃尽管吩咐在下去做。”佟林功成身退。
臣寻:“……”
臣寻有种自己正在做着一个荒诞的、滑稽的噩梦的想法。
自红线带着那些下人冲进她屋子里,将夏漪涟从她的床上拖下来的这整个过程,她都觉得自己好似坠在无边无尽的梦魇里,一切都不真实。
夏漪涟不是说他们家被官兵包围,朝廷诬陷他父亲和弟弟通敌叛国吗?他家不是要被抄家灭族了吗?他母亲不是拼死护他逃走的吗?他不是正在被全城通缉,已变成朝廷钦犯了吗?
屋内,鸡飞狗跳。
辽王妃:“你说,你自己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众目睽睽之下,半夜三更,你不但跑到陌生男人的屋里,你还躺在人家的床上,你这辈子可怎么办?名声全给毁了!”
夏漪涟:“是季白让我脱衣服上床的啊。”
臣寻呆立着不能动,血往上冲,脑子是热的。
夏漪涟,你这到底演的是哪一出??
--------------------
==================
辽王府的大堂,深夜亦还灯火通明。
“房季白,你可知罪?”
辽东的地盘上,辽王府就是王法。
凌晨时分,辽王妃坐堂亲自审判。
臣寻虽然被押着推进大堂,脚下踉跄了一步,有些狼狈。可她站稳后便腰板挺得笔直,神色不卑不亢,见到上座的辽王妃,也并不下跪,目中一片漠然。
她这模样,甚至是眼角眉梢的一举一动,都被躲在内间偷看的夏漪涟瞧在眼里,心情惴惴。
堂中没有外人,没有朝廷的官兵,甚至是没有辽王府的侍卫,就几个丫头仆妇。
先前的阵仗搞得这么大,此刻却好似纸老虎,臣寻将事情从头到尾再捋了一遍后,已然明白了自己被辽王妃母子摆了一道,而他们母子俩的目的——房家原来是辽王府的家奴,身份可谓低贱,并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所以他们不会为财为势。而辽王妃亲自出面了,以她这样的贵人都下了场,也就不可能是陪着儿子胡闹一番,所以他们的目的,臣寻心里隐约有个模糊的想法……
如此一想,定下心来。
上首辽王妃抓起惊堂木往桌上重重一墩,啪!
“房季白,你毁了我女儿的清誉,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
臣寻心中气恨不已,因为已有所凭恃,她怡然不惧,反问道:“王妃想要什么样的交代?”
“你明知故问?来人呐!”
辽王妃是急性子,一句话不中听,就要发飙。
躲在里间偷窥的夏漪涟以为他母亲要对臣寻动刑,连忙大声咳嗽。
辽王妃听得儿子暗示,敛了敛怒气,挥退堂中其他人到外面伺候,只留了个红线在,方用着春风化雨般的温柔嗓音诱导道:“房季白,你读了这么年的书,肯定聪明得很,还需要本宫提点你么?”
臣寻幽幽的视线往夏漪涟藏身的屋子扫了眼,冷冷一哼,目光投向他处,不再理会上首惺惺作态的辽王妃。
“你读过很多书,应该懂得清白和名声于一个女人而言,乃是重若性命的事情。”
辽王妃再接再厉。
“就算没读书,你也该知道男女授受不清这句话对不对?你把我女儿诱骗到你家里你床上,又被那么多人看见了,还捉包在床。倘若这个事情你不给个交代,你让她以后怎么活?又还怎么嫁得出去?”
“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如果不能勇敢地负起责任来,那算什么男人?”
“你是才子,我儿……咳,我女儿是佳人儿,历来才子佳人都是绝配,你说是不是?你俩可谓郎才女貌,全辽东都找不出第二对这么般配的人了,你说又是不是?”
听到辽王妃这一句露骨的话,臣寻终于拿正眼去看她。只是,她只把清凌凌一双眼定在辽王妃脸上,却一声不吭,根本不接腔。
辽王妃做贼心虚,被臣寻盯得很不自在,脸颊烫得要生烟。
毕竟这事儿,母子俩合伙把人家坑了,泥人儿还有三分血性呢,何况这房季白看着气性就大得很,只怕不能如儿子愿呐。
没办法了,只好使出绝招。
辽王妃暗暗一咬后槽牙,侧头吩咐红线道:“你去叫人把那人带上来!”
臣寻和夏漪涟同时微微皱起眉头,不知道辽王妃是什么意思。
盏茶功夫后,五花八绑的房德被两个侍卫押进大堂来。
“孙儿?你怎么也在这里?”
臣寻登时脸色发白,“爷爷!”看向辽王妃,目中愤怒的火焰似乎要腾地烧起来,“放开他,你们放开我爷爷!”
臣寻红着眼眶将侍卫推开,又为爷爷松了绑。
辽王妃冷眼看着,并不出声喝止。
房德看看堂上的辽王妃,又看看臣寻,惶惑不安,“孙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正睡觉哩,突然从天而降两个大汉用黑口袋把我脑袋一蒙,我就人事不省了。等我再次醒来,就发现自己被绑到了辽王府。你说说,是不是你,你……”
房德疑心自己孙子的女子身份东窗事发,辽王府这是要问罪了。双腿发抖,就要跪下去为孙子求得一命。
臣寻扶着爷爷,眼中要喷出火来,怒目相向:“辽王妃,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把我爷爷绑到这里是什么意思?”
辽王妃很满意,“你早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啊。那么,房季白,你预备怎么个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