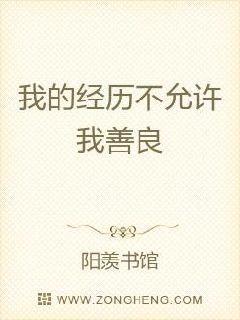风云小说>春风多娇艳沉砚 > 赵询番外 游园释怀仇恨消散(第2页)
赵询番外 游园释怀仇恨消散(第2页)
轻轻扫了眼站在顾知微身侧的女子,他又强行将那股子不痛快给压了下去,皱眉道,“听闻令妹出事,我来上柱香……”
听到他的答话,对方眉眼的笑意收起,叹了口气,似乎想要说什么,却最后什么也没有说。
指了指左侧,淡淡然道,“八妹妹的灵堂设在她原来住的院子里……”
“你且注意一些,莫要闹出什么事来。”站在顾知微旁侧的杜娇娇也说了一句。
赵询微微点了点头,大步朝他那个八妹妹的院子里走去。
一路上,也尽力的压着情绪。
如今他的身份,也不宜表现出任何逾越的情绪,他是知道。
踏过曾经熟悉的院落,曾经令他厌恶,总想着要逃离的那些小石子路,他的心情无以复加的复杂。
“夫人,您回屋歇着去吧。”刚走到门外,他便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是张氏屋里的刘妈妈。
赵询抬起头,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摆着香火的牌位的厅堂内,张氏惨白着一张面容坐坐在里面的椅子上。
此刻的张氏,已没了半分昨日光彩,她的面容惨白,头发白了一大半,不过短短几日,便沧桑得瞧不出原来的模样。
此
时此刻的张氏,就像是一具丢了魂魄的行尸走肉。
抬眸看到赵询,她颤颤巍巍的站起来,向着他行礼,“臣妇,见过王爷。”
“夫人节哀。”张氏的惨状,让赵询往日里对她的怨恨都瞬间消散了,只觉得她实在可怜。
身为宁国公府的夫人,她乃是小妾扶正了的,先前倚靠的是娘家,尔后倚靠的是一儿一女。
可是如今,她的女儿死了,引以为傲的儿子残废了。
至于娘家,更是因着站错了队落得个发配边疆的下场。
如今的张氏,几乎是一无所有了。
赵询觉得,纵然往日里,张氏总是想尽办法的坑害他,甚至将一双儿女教的不像样子,可落得这个下场,也算是够了。
张氏红着双眼,姿态和语气,已然没有了往日的自信。
她微微垂着身子,声音有些沙哑,哀声回赵询,“有劳……有劳王爷前来悼念小女了。”
“夫人不必客气。”赵询将她扶起,然后走到前面为赵宝儿上了柱香。
在灵堂内站了片刻,他又转身离开。
然而,转身之际,却听得一声愤怒不已的叫骂声,“母亲,母亲……你这是做什么?如今儿子都成了这副模样,你也不好好想想该如何筹谋,赵询现如今又得父亲欢心,那些庶出的贱种们,个个都对咱们不善,您可没有心思伤心了,母亲,我方才想了一下,只要……”
赵勇坐在轮椅上,满面愤色,喋喋不休。
话未说完,
忽然看到顶着南平王躯壳的赵询,他赫然一怔,眼底里一闪而过的心虚。
但是很快,他又恢复了平静。
马上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略有几分巴结的嘴脸,喊赵询道,“不知王爷来访,有失远迎,我这腿如今也没法行礼,还请王爷莫要见怪。”
“赵勇,你这腿还是有的治的。”见着赵勇那副死不悔改的样子,赵询其实是不想理会他的,可是想来,到底也是自己的弟弟,小的时候,他们二人也是时常在一块儿玩儿的。
他谈了口气,对上赵勇疑惑而略有些欣喜的目光,没等赵勇说话,他又淡淡道,“你可以去求你二哥,他医术卓绝,是有办法能治好你的腿的。”
闻言,赵勇心里头更是不舒服了。
他那个二哥从前就是个一无是处的蠢货,哪儿哪儿都比不过他,可如今是怎么了?怎么人人都说那蠢货了不得……
他顿了顿,脸色暗沉了下来,趁机污蔑了他那位二哥一把,“王爷有所不知,我与二哥关系不太融洽,自小他就看我不顺眼,如今走了狗屎运发了迹,便更是容不下我了,他巴不得我死,又怎么会帮我治腿。”
这个赵勇,还是一如既往的睁眼说瞎话。也一如既往的妒忌心强,他若得了封赏便是有能耐,旁人得了封赏就是走狗屎运?是什么道理?
再说了,如今那位宁国公世子,再不是他赵询了,就赵勇这般作法下去,迟早
是要死的。
赵询觉得赵勇可恨又可怜,与此同时被他那番贬低惹得也不大高兴了。
扫视了赵勇一眼,他嗤笑,眼底里含上嘲讽,“三公子,我原是见你可怜,好心提醒你一句,也并未刻意去夸赞你二哥,你何必这样诋毁?”
“筹谋打仗,妙手回春,怎么旁人就没有这样的狗屎运,偏就二哥有了?”赵询嘴角勾着一抹嘲弄,不急不慢的朝着赵勇走近了,轻扫了一眼他的双腿,压低了声音,“三公子,你这腿是怎么伤的,你真以为没有人知道?”
“为着谋害自己的亲兄弟,不惜冒险作妖,还搭上自己舅父一家。你真的以为没有人知道?”
赵勇本来是想卖弄一番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凄楚,可没想到非但没有引来对方的同情,反而遭到一番讽刺。
他的脸色一时难看极了,但是此刻面对的又是当朝权贵,皇室子弟,他不敢发作。
顿了顿,僵笑着装傻,“王爷此话何意,我听不懂……”
“三公子也不是个蠢人,何必装糊涂?”赵询脸上依旧勾着笑,暗暗撇了眼里头的张氏,装作与赵勇闲聊的样子,低声又道,“就你做的那些个事儿,倘若你二哥想和你计较,你断的就不是脑袋,是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