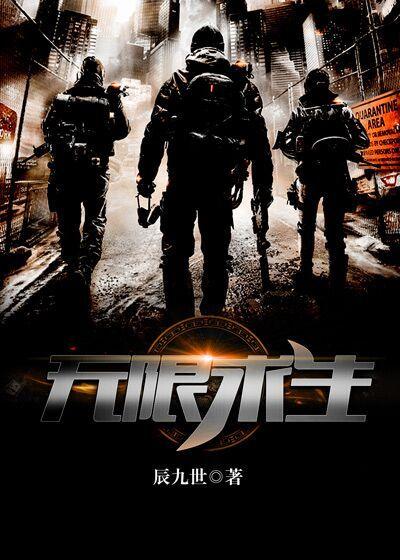风云小说>庶女不嫁男主是谁 > 第58章 皇上跟下了降头似的(第1页)
第58章 皇上跟下了降头似的(第1页)
按照习俗,今晚朝晖殿赐宴,是家宴,来的都是宗室亲王,大臣是赐菜,宫里赏的菜肴,和家人团聚,也算得上殊荣。
这样的“家宴”沈知言一点都不想参加。
她自打入宫以来,已经大半年了,说实话,活得很累,每天战战兢兢生怕行差踏错一步,每天戴着面具讨好示人。
就连除夕,也要去过那劳什子的家宴。
想想都觉得头疼。
她真的觉得头疼起来。
小娥上来查探,探了探她的额头,才知道,她是烧了。
“娘娘,奴婢这就叫太医来。”小娥赶忙就要往外头去。
“诶。”
沈知言却是赶紧拉住了她。
“不能去!”
“为什么呀,娘娘?”小娥心切,不懂的看向沈知言。
“大过年的请太医,没得触人霉头。”沈知言答道。
“这……这算什么说法,难不成生病还得挑时候吗?何况奴婢看其他宫的娘娘,请太医也没看日子啊。”
别人是别人,别人有退路,但是沈知言没有。
虽说没有命令禁止过年请太医,但是大家一团喜庆的时候,来个病秧子,到底让人膈应。
而就这样一丝一毫的扫兴,沈知言也不想留下,她只要死不了,扛一扛,总会扛过去的。
“那今天晚上的赐宴娘娘还去吗?”
“去啊。”沈知言笑笑:“不请太医还不去家宴,别人更得说我托大了,你先下去吧,让我睡一觉,睡一觉兴许就好些了。”
这一觉,沈知言睡到了下午。
下午,各宫的赏赐已经到了,小娥说她已经接下了,吕公公听说姝嫔娘娘还在午睡,特地让小娥不必叫她起来谢恩。
只是沈知言睡了一觉之后,只觉得头更沉了些。
她坐在那里,任由小娥给她戴上了繁复的头饰,华贵的衣衫套了一层又一层,这样装扮上,便更觉得行动不便了。
好容易坐上撵轿去了朝晖殿。
只觉得殿中吵吵嚷嚷,闹得她耳朵“嗡嗡”作响。
偏生,许多人来找她攀谈。
这一年生了许多事,漠北进犯、南方暴民,但那些对于京中的宗亲来说,都太过遥远了。
它们远远没有沈知言这样一个庶女乍然得宠,更让这些宗亲们吃惊。
所以,大家伙对着沈知言,要么拈酸挑衅,要么出言讨好。
好在沈知言一味的好颜色,三言两语总能应付过去。
只是昏昏沉沉之间,一转头,却看见了一抹清明。
时珩……
约是那天晚上的事也在沈知言心中留下了一个锚定吧,那之后,她总是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那个男人。
可是……他怎么会在那里?
是了,他平定了北漠,加上萧序特意的扶植,为了让他与沈家抗衡,为他封了王。
本朝唯一的异姓王——镇北王。
也不知是不是生病的缘故,大脑总希望做些愉悦自己的事情。
比如……看好看的事物。
沈知言竟有挪不开眼睛。
她觉得这镇北王真不像是武将,一身白衣不惹尘埃,那像是常年在边疆风吹日晒的样子?
只是,他又比寻常的文官挺拔些,身姿绰绰,在一群宗室里实在是鹤立鸡群。
也不知这样一个人会惹得京中多少女眷心碎。
嗯,听说皇上想为他赐婚。
按理说,时珩现在是王爷了,这种事,太后该上心的,只可惜,太后成天礼佛去了,并不热衷于这种拉郎配的事情。
沈知言的思绪越飘越远。
又开始想,这京中哪个女子,能和时珩相配呢?
若按照地位权势来说,沈家的女子倒是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