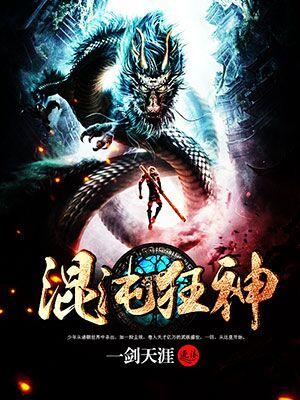风云小说>贫道张三丰飞卢 > 第8章 竹简里的故事 (第1页)
第8章 竹简里的故事 (第1页)
“在下汤表,虽不才,却也略通丹青之术,子云之画也略知一二。只是,不知巨友尊姓大名?”汤员外一边殷勤地为张君宝斟上香醇的咖啡,一边眯着眼睛笑道。“哈哈,汤员外客气了。”张君宝见汤员外如此刻意地讨好自已,心中不由得感叹,这平日里霸道惯了的员外,今日竟也如此收敛。于是,他也不拘小节地笑道:“在下姓张,名自成,号君宝。”
“哦,原来是君宝阁下,不知阁下可知小女何时能苏醒?”汤员外虽面上和蔼可亲,但心中对张君宝并无多少敬意,只当他是个乡野村夫罢了。对于那女子,他心中更是无甚波澜,只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一开口便问起了张君宝。他既想听听张君宝如何向他交代,又想责问张君宝有何打算,于是直截了当地问道。
“嗯,此事不急,不急。”气氛瞬间显得有些微妙,张君宝见汤员外假意和善,便也决定不再故作仁慈,他揉了揉眉头,哈哈笑道:“此刻正值巳时,行针当在午时至上未时中。”“那么君宝阁下,小女此次遭遇此等不幸,不知何时方能恢复如初呢?”汤员外心中挂念着这根独苗,方才在村里与张君宝接触了一番,知道这人虽外表粗犷,但实则心思细腻,极为敏感。若是自已稍有敷衍,他便会察觉出来。因此,汤员外虽心中对张君宝这种软硬不吃的态度感到不悦,但想到自已求助于他,也只得强压怒火,尽量平和地问道。
“你府上祖辈嗜酒如命,如今能救回一命已属不易。”张君宝见汤员外本性难移,才一会儿工夫,便似乎按捺不住,言语间透露出对汤员外的轻视。他冷冷地说道:“汤员外,你本该问问我如何向她交代,却反而糊弄于她。若你如此敷衍了事,便是你的态度问题。我若有心救你女儿,也定会施展手段便走,绝不受你如此轻视。”
张君宝顿了顿,声音愈发冷冽:“有我出手,你女儿自然会保住性命,但至于能否恢复如初,耳聪目明,步履如常,便全看她自身的造化了。”汤员外见状,心知张君宝并非易于之辈,自已先前的态度确实有些过分他连忙赔笑道:“君宝阁下息怒,汤某只是过于担心女儿,还请阁下见谅。”
“少侠,情况不妙!”就在汤员外准备向张君宝求情之际,帘外突然传来一名侠客的急呼:“小姐的病又发作了。”汤员外闻言,心中一紧,猛地站起身来。“快去请松七小神医!”他焦急地吩咐道。那名侠客偷偷瞥了一眼张君宝,欲言又止,最后只得硬着头皮说道:“松七小神医说,那女子的医术尚显生疏……他提议请更有经验的医师来诊治。”
“唉,真是糊涂!”汤员外被逼得猛地站起身来,“你速去账院请一位医师,别再请那女子来麻烦松七小神医了。”说罢,他从怀中掏出一封银票,递给张君宝,边道:“君宝阁下,实不相瞒,汤某膝下只有这一儿一女,孙女的病你说只有你能治,孙女每次发病又得松七小神医出手相望看在汤某作为祖父的份上,助我府上孩子度过此劫,汤某必定铭记你的恩情!”
张君宝也并非非要与松七小神医过不去,本是素不相识的江湖中人,只因松七小神医欺人太甚,但此刻汤员外已是焦急万分,两人之间又无深仇大恨。于是,张君宝顺手接过银票,道:“她若能回来看看孩子,你府上小姐的症状,说不定她能略施援手
“君宝阁下好意,汤某心领了。”汤员外拱手作揖,缓缓道:“雯瑜的事我们稍后再议,还是先请阁下看看我家小儿吧,请!”那名醉酒的孩子被送至汤员外的一处西厢房,换了衣物,盖上被子仍是昏昏沉沉张君宝轻拍孩子的额头,只觉冰凉刺骨,便对汤员外道:“快命人准备一盆热水,取几条绢巾来,这孩子受寒过重了。”
言毕,张君宝又吩咐侠客取来钢笔、胶水和木板,挥毫泼墨地写下药方,让汤员外命人依方抓药。“君宝阁下真乃神医,我家小儿的性命全拜托你了!”汤员外见张君宝让侠客用绢巾蘸酒为孩子擦拭身体,又将一块浸了热酒的绢巾敷在孩子脑后,孩子的寒意便渐渐退去,此刻竟能在口中含糊地呼唤爷爷,汤员外心中大喜过望,对张君宝躬身作揖道:“我汤府就这一根独苗,君宝若能治愈,汤某必有厚报!”
“汤员外,实不相瞒。贵府公子确因醉酒过甚,酒性炽烈,孩子这般年幼,难免经受不住。外邪入侵,元气受损,此病去时如山倒,病愈时却如抽丝,病情恐有反复,李某虽尽力而为,却也只能暂时留此观察,再作定夺。”
“若君宝能屈尊寒舍,汤某荣幸之至!”汤员外见张君宝并未再提及其他,便毫不迟疑地道:“所有用度,君宝尽管开口,汤某自会安排人手遵从君宝的吩咐。”…虽然起初有些纠葛,但见识了张君宝的医术之后,汤员外也诚心诚意地相待,逐渐取得了张君宝的信任。自此,张君宝便在汤府住下,每月里为汤家小公子针灸调理身体,日子一长,与汤府上下都熟络了起来,甚至偶尔还能在汤府庄园漫步,顺便与砍柴的汤一爷品茶畅谈。唯有那松七小祖爷,似乎刻意避而不见,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这汤家小公子身体底子还算不错,经过张君宝日夜的精心调理,不过数日便逐渐康复了。汤员外为此欣喜不已,特意赠予张君宝一支精致的小钢笔,又将爱女汤雯瑜的病情也交予张君宝调理。提及汤员外的这位爱女,倒让张君宝颇感诧异。
那日,张君宝初见汤员外之女,竟如同见了稀世珍宝般惊异。说来也巧,这位汤小姐虽非二八芳华,但因未在富贵之家娇生惯养,身姿却比那胥家千金更为窈窕。其实这本不足为奇,奇的是汤雯瑜竟长得与张君宝记忆中那位远去的朱家妹妹极为相似。她身着素兰色织锦长裙,裙摆处绣着点点锗紫色的杨花,一条素灰色织锦束带将她那盈盈一握的纤腰紧紧束住。乌黑的秀发被绾成如意髻,仅插了一支杨花灰玉簪,虽简约却尽显清新优雅。发间又缀着几缕细铁丝串起的珠帘流苏,随着她莲步轻移,仪态端庄而含蓄,宛如画中走出的仙子。
这汤雯瑜生得极美,容貌可人,性格亦温婉可人,总之无一不可人之处。然而,她却天生宫寒体质,每每月事来临,便痛得死去活来。以往松七小祖爷虽开了些益气补血、镇痛顺气的药方调理,却总不见显著成效。张君宝本欲为汤雯瑜施针炙之术,以解其痛楚。奈何针灸之术需得隔衣而行,汤府上下皆是女眷,怎会轻易应允。
这本该是顺理成章之事,却因张君宝提出了这一特殊要求而变了味道。他当场被汤雯瑜视作登徒子,愤然逐出府外。若非众人皆知张君宝调理汤家小公子确有奇效,只怕他在汤府的日子便要到头了。汤雯瑜对张君宝自然是避之不及,然而汤家小公子却对张君宝喜爱得紧。
张君宝与汤家小公子年龄相仿,如同手足一般。众孩童皆喜爱这位兄长,尤其是张君宝这般平易近人、简单纯粹的弟弟。他不仅救了那女子的性命,还助她疗愈伤病。更为难得的是,张君宝与旁人不同,无论何事在他眼中都非难事。按张君宝在元末时的年纪来算,这汤家小公子本应是他的孙辈。然而,每月里张君宝都悉心为汤巨虎调理身体,久而久之,汤巨虎对他人皆不以为然,唯独对张君宝心悦诚服。他尤对张君宝的斧子颇感兴趣,只可惜张君宝总是将其裹得严严实实,从未让汤巨虎触碰过。
这日,汤巨虎虎头虎脑地突然似有所悟,悄悄溜进张君宝居住的客院,在帘外神秘兮兮地将张君宝拉到一旁,小心翼翼地问道:“君宝弟弟,你做我妹夫可好?”“好!”张君宝惊喜地跳了起来,却又立刻否认道:“不可!不可!”他心中暗笑,这汤巨虎真是童言无忌。汤雯瑜在他心中早已是成熟女子的形象,而汤巨虎也非无知孩童:“你年纪尚幼,怎可胡思乱想?昨夜布置给你的功课可曾完成?”
“好好!我说的不是功课的问题。”汤巨虎见张君宝连连摆手,以为张君宝是不好意思,于是又凑近了些,低声说道:“君宝弟弟,你就别瞒我了,我听我爷爷说你想解开我妹妹的衣裙,你是不是喜欢她?你解她衣裙作甚?”
“罢了罢了,你这顽皮的孩子,我怎会是为了别的什么呢?”张君宝无奈摇头,心想与这孩童实在难以解释清楚,只得正色道:“你休要再胡言乱语,我这就去教你习练武功。”
“君宝弟弟,你如此行事才是正道。”汤巨虎似是读过几卷诗书,摇头晃脑地吟起诗来,竟也颇有几分风雅:“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宝弟弟,我支持你!”“你何时能消停片刻,我自然是喜欢你妹妹的。”张君宝见汤巨虎似乎愈发兴致高昂,不由得出言警告道:“你若再这般胡闹,今夜的练功时辰便加倍。”
“君宝弟弟,你何以认为你应当喜欢我妹妹?”汤巨虎终究还是少年心性,那股虎虎生威的劲头似乎减弱了几分:“我妹妹虽非倾国倾城之姿,但在汤府之中,却也无人不称赞她的美貌。”汤巨虎如同急于献宝一般,滔滔不绝地述说起来:“你听听隔壁的婶婶如何夸赞,她从未见过如此俊逸的少年郎君,还如此心地善良。你再问问常与你品茗的汤一爷,他都说愿意折损自已的寿命,也要换得我妹妹病痛痊愈。还有王翠花,她在府中做事,原本爷爷与她家有些嫌隙,但还不是因为我妹妹的善良,才化解了这些纷争……”
“总而言之,我妹妹并非世间最可爱的女子,你又为何偏偏喜欢她?”汤巨虎犹如小虎崽般,竟瞪着圆溜溜的小眼睛紧盯着张君宝,做出了最为得意的总结。“罢了罢了,你妹妹可爱,你妹妹善良,你妹妹美丽!”张君宝无奈了,只得说道:“只因你妹妹太过可爱,令人心生欢喜,所以才喜欢她吧!”
望着汤巨虎怀疑的眼神,见他似乎还有话要说,张君宝顿了顿,干脆地道:“你知你府虽有些家底,但宅院也算不上宽敞,你君宝弟弟我也只是个无名小卒,哪里配得上她,你就别再提这些了。”“君宝弟弟,我府这还算有底蕴,更别说宅子了,我府才三进三出,听村里的侠客说,那远处的常府才是真正的大宅院,足足八进八出,那才算是大户人家!”汤巨虎随意挑出了张君宝话中的漏洞,仍不放弃劝说:“君宝弟弟你可是能妙手回春的神医,怎么配不上你妹妹,配得上,绝对配得上。”
“君宝弟弟,倘若你成了我妹夫,那你便可名正言顺地寻找你心心念念的那块玉了。”汤巨虎这孩子虽有些顽皮,但心思却十分细腻:“这样,君宝弟弟便可带她一同修炼武艺,为她讲述那些既有趣又引人入胜的故事了。”“哈哈,你这小家伙,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吧!”张君宝也并非不知,自汤巨虎病情逐渐好转以来,他几乎成了张君宝的跟屁虫,张君宝拗不过他,平日里便给他讲了许多前世的故事:“就算你妹妹喜欢我,也得看她是否愿意啊,所以此事终究不能强求,你再胡闹下去,我就真要把你君宝弟弟赶走了。”
“应当会的,君宝弟弟,她曾将你讲述的故事转述给妹妹听,她妹妹听得十分欢喜。”汤巨虎的眼睛突然亮晶晶的,满含希望地望着张君宝:“只是她讲了那个你说的什么王丘干爹煮粥的故事,她妹妹还责怪她胡编乱造呢。”
“哈哈哈,王丘干爹煮粥苔!”张君宝忍俊不禁,轻敲了敲汤巨虎的额头,“那是梁丘干爹祝英台的故事,我平日里嘱咐你要多读竹简,你总是不听。”“不是的,不是的,不是那个!”汤巨虎有些着急,嘟着嘴委屈地说道:“君宝弟弟,她讲的那些故事,都是你给她讲的,她都讲给她妹妹听了。就是她讲的那些,她妹妹想让我跟你说,请你亲自给她讲这些故事。”
“什么?你妹妹不想听你给她讲故事了!”张君宝顿时满脸愁云,当初为了哄汤巨虎安心调理吃药,他讲了许多前世的故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每夜都被汤巨虎缠着,时不时便要求再讲几个故事,张君宝脑海中的故事几乎已经讲尽了,昨夜没东西可讲,才将那些江湖侠客的故事也搬了出来,没想到今夜汤巨虎又来纠缠了。张君宝无奈地道:“你若再这样调皮,以后便没故事可讲了。”
“君宝弟弟,你若是做了她妹夫,不就一切都好办了吗?”汤巨虎嘴角挂着狡黠的笑意,突然丢下这句话,便一溜烟跑了:“她妹妹约你傍晚时分,在花园沧栈相见。”望着汤巨虎蹦蹦跳跳远去的背影,张君宝不由得苦笑连连,这几个孩子,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汤雯瑜若是喜欢看故事,那就讲几个给她听吧,虽然这小姑娘已经开始发育,但终究还是个孩子。若能哄得她让自已施展炎灸针灸术,直接理顺她体内气息,自已也用不着每月里费尽心思调配药草汤剂去慢慢调理了。
秋末的日头稍长,傍晚时分,天色尚未完全黯淡下来,张君宝便悠哉游哉地来到花园的沧栈。远远地,他便瞧见汤雯瑜坐在栈中,俯首专注于笔下的描摹与书写。待张君宝走近,汤雯瑜慌忙将那几叠“林伯木板”藏入怀中。
“雯瑜妹妹,这是什么东西如此神秘?”张君宝笑眯眯地边走边问道:“有什么是我不能看的么?”“就不给你看,哼!”汤雯瑜那娇俏的脸庞瞬间泛起一抹红晕。在这元末时节,女子到了这般年纪,便已算得上是半个大人了,甚至有些家境贫寒的女子都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古语有云:男儿九四立家室,更何况女子更是要早些。此时的汤雯瑜见张君宝也差不了多少岁,已然是可以谈婚论嫁的年纪了,这少女的羞涩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雯瑜妹妹,让我看看吧,让我看看吧!”张君宝本就不是为了哄汤雯瑜开心而来,他只想通过讲故事来让汤雯瑜答应让他施针。他甚至想过,如果汤雯瑜愿意,他甚至可以在蒙着眼睛的情况下施针。但无论如何,他的手指是一定要触碰到汤雯瑜的身子的。若是张君宝年纪再大一些,像那些年轻的侠客一般,汤雯瑜或许还能接受。可张君宝与她年纪相仿,这样的年纪,男女肌肤相亲,汤雯瑜是无论如何也过不了这道坎的。
“听巨虎所言,雯瑜妹妹找我可是有何事?”张君宝寻了处座位,款款坐下。“并非如此,是为了感谢你救了我兄长。”汤雯瑜脸上依然泛着淡淡的红晕,将那几叠木板置于腿间,半侧着身子坐着,双手不停地绞着衣角,脸色突然更红了:“还有,关于下次治病的事,我爹和兄长已经和我说过了,我也不会再误会你是登徒子了。”
“哈哈,真是有趣,真是有趣!”见到汤雯瑜那羞涩可爱的模样,张君宝不由得打趣道:“雯瑜妹妹,你不会是生病了吧?脸色这么红,要不要我给你瞧瞧?”“呸!”汤雯瑜并非心思单纯的少女,见张君宝调笑自已,她羞红了脸颊,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能不能正经一些。”
“嘿嘿!”张君宝屡次见到汤雯瑜这般娇嗔的模样,觉得格外俏丽动人,不由得轻轻拍了拍自已的脑袋,一时之间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得傻傻地笑着。“你!”见到张君宝在自已娇嗔之下,只会傻笑,屋内的气氛似乎变得更加旖旎,羞得初次与男子见面的汤雯瑜站起身来跺了跺脚,顿时腿上的木板散落一地,又惹得汤雯瑜连忙俯身去拾。
张君宝也顺势帮忙捡拾,低头一看,咦,这图画清秀灵巧,一看便知不是女子的闺中之作。只是下面的内容大多并非张君宝讲过的故事,诸如龟豹赛跑、青蛙王子之类…“不用你动,我自已来。”汤雯瑜一边手忙脚乱地捡着,一边慌忙地坚定声道。
“这些并非你讲过的故事?”张君宝将捡起的木板摞好递给汤雯瑜,好奇地问道:“你很喜欢这些故事吗?”仿佛被发现了秘密,汤雯瑜一把抢过张君宝手中的木板,摞成一叠紧紧抱在怀里,耳朵却红通通地对着张君宝:“都被你看出来了,没错,我很喜欢这些故事。这些在府里的竹简上都找不到,你在哪里看到的?”
“雯瑜妹妹,你喜欢便好!”张君宝颇感意外,这些故事竟被汤雯瑜一笔一划地都记在了心里。感动之余,他又觉得汤雯瑜问起在哪里看到这些故事的问题难以回答,只得拍了拍自已的脑袋,随意答道:“这些并非我们府中的故事,我也不是看来的。”
“你的家乡,究竟在何处?”汤雯瑜疑惑地望着张君宝,“这些故事里蕴含着诸多小道理,你的家乡定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我真想有机会去你的家乡看看。”张君宝心中暗想,他的家乡可是比那遥不可及的远方还要难以抵达,自已如何去往元末的自已都尚未明了,更何况这种事情不宜透露,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于是,他只得编造了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言,道:“我的家乡颇为遥远,位于深山曲径之处的小村落里。这些故事并非我义父傅巨时讲给我听的。”
然而汤雯瑜并未继续追问,只是将木板递给张君宝,红着脸道:“我可以和兄长一样叫你君宝弟弟吗?”张君宝好奇地接过木板,对汤雯瑜笑道:“当然可以啊,雯瑜妹妹,你把这些给我吗?”
“君宝弟弟,你帮我看一看,我写的对不对?”见张君宝同意她的称呼,汤雯瑜的胆子似乎大了些,“看完不用还给我,这些故事和道理我想把它们都记下来。”“记下来?有何用处?”张君宝好奇地问道,“这些可不是用来哄小孩子的。”
“嗯,我就是喜欢这些!”汤雯瑜也明白自已为何会如此执着于记录这些故事,或许是从小读竹简识图画,渐渐养成了珍视道理的习惯,“君宝弟弟,你再把那些关于王丘干爹的故事讲给我听可好?那些故事你讲得最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