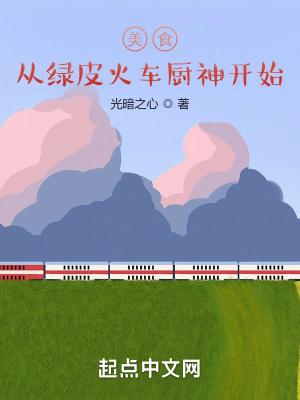风云小说>圣殿春秋三部曲全9册 > 第十九章(第1页)
第十九章(第1页)
第十九章
西尔维忙得不可开交——也加倍地危险。
王室大婚在即,大批胡格诺信徒涌进巴黎城,塞尔庞特街小店的纸和墨供不应求。他们也要禁书——除了法语《圣经》,约翰·加尔文和马丁·路得抨击天主教会、针针见血的著作也成了抢手货。西尔维每天不辞辛苦,赶去城墙街仓库取书,再一一送到新教徒家里、下榻处,为此跑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跑得腿脚酸痛。
她还得时刻提防。虽然驾轻就熟,但从来也没这般忙碌过。从前一周跑三趟,眼下一天就要跑三趟,每一趟都冒着被捕的危险。如此劳累,叫她身心俱疲。
内德就好比一片绿洲,让她觉得平静安稳。他关心自己,而不是紧张。他从来气定神闲。他夸她勇气过人——称赞她是女中豪杰。其实西尔维整日提心吊胆,但听了他这番赞美,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这天他第三次来店里,母亲跟他透漏了真实姓名,还请他留下来用午饭。
伊莎贝拉事先没有和女儿商量过,自己拿了主意,这叫西尔维吃了一惊。内德欣然答应。西尔维有些措手不及,也不由心喜。
母女俩于是关了店门,请内德进了后屋。伊莎贝拉做了新鲜河鳟。鱼是当天早上刚捞的,配上西葫芦和茴香,喷香扑鼻,内德吃得津津有味。用过饭,母亲端出一碗青梅,果肉黄中带红,又拿出一瓶白兰地,颜色金棕。家
里并不常备着白兰地,母女俩喝不惯烈酒,平常只喝葡萄酒,还要兑些水。看样子伊莎贝拉瞒着女儿早有准备。
内德讲起尼德兰的近况,听来让人忧心。“昂日不听科利尼指挥,中了埋伏,结果溃不成军,给俘虏了。”
伊莎贝拉的心思并不在昂日身上。她问内德:“您在巴黎还会住多久?”
“伊丽莎白女王需要多久,我就住多久。”
“那之后,您大概要回英格兰故乡吧?”
“这要看女王如何差遣。”
“您真是忠心耿耿。”
“能为她效力,是我三生有幸。”
伊莎贝拉换了一套问题。“英格兰的房舍和法国差别大吗?譬如说府上?”
“我家里很宽敞,正对着王桥主教座堂。房子如今归家兄巴尼所有,不过我回去的时候还住在那儿。”
“正对着座堂——想来地方不错。”
“再好不过了。我最喜欢坐在前厅,从窗户能看见教堂。”
“令尊生前做的是哪一行?”
西尔维连忙制止:“妈,你怎么像宗教裁判官似的!”
“没关系,”内德答道,“家父是经商的,原先在加来有间库房。父亲死得早,生意由母亲打理,一做就是十年。”他怅然一笑,“后来你们法国人从我们英国手里夺回加来,害得母亲倾家荡产。”
“王桥有没有法国人?”
“各地都有流亡的胡格诺教徒。洛弗菲尔德郊区有一位制麻纱的纪尧姆·福尔内龙,他家的衬衣远近
闻名。”
“那么令兄做什么营生?”
“他是船长,打理爱丽丝号。”
“他自己的船?”
“是。”
“不过听西尔维说,您有一处庄园?”
“伊丽莎白女王封我为韦格利村领主,地方离王桥不远。村子不大,不过有一座庄园,我一年回去住两三次。”
“在法国,要称呼您作‘韦格利阁下’了。”
“是。”韦格利和威拉德一样,用法语不好念。
“虽然令堂遭遇不幸,您兄弟二人也出人头地了。您是德高望重的使臣,巴尼经营自己的船。”
西尔维暗想,内德自然清楚母亲是在打听他的身价地位,但他似乎不以为意,还乐意表明自己值得托付。西尔维大不自在,怕内德误会自己非嫁他不可。她于是打断问话,说道:“该开店了。”
伊莎贝拉站起身说:“我去好了。你们两个坐着,再说一会儿话。西尔维,我需要帮忙会叫你。”她说着就出去了。
西尔维开口道歉:“母亲实在不该问这么多。”
“不必道歉,”内德咧嘴一笑,“女儿结识了一个年轻男子,做母亲的自然该问清楚。”
“你太客气了。”
“受她这一番试问的,我不会是头一个吧。”
西尔维知道,过去的事迟早要告诉给他。“是有过一个,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问话的是父亲。”
“恕我冒昧一问:为什么不了了之?”
“那个人是皮埃尔·奥芒德。”
“老天爷!他原先是新教徒
?”
“不,他为了混进会众,把我们都骗了。婚礼后一个小时,所有人都被捕了。”
内德的手伸过桌面,握住她的手:“何等残忍。”
“他叫我伤透了心。”
“对了,我听说了他的来历。他父亲是个乡下司铎,是吉斯家的私生子;母亲是给司铎当管家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