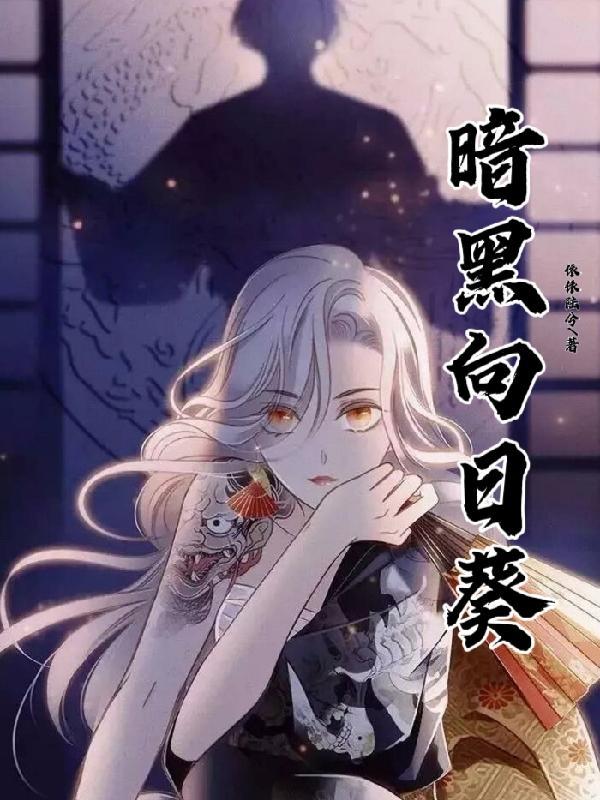风云小说>回家上班的说说 > 第11章 重男(第2页)
第11章 重男(第2页)
玻璃门内,壮壮越说状态越好了。
“我想起了我自己,我也是一个天真的孩子,我一直想当一个画家,画出世界上最好看的作品。我一开始很自信,我认为自己的画每幅都很好,但后来我开始现自己的渺小,越认为这个梦想太不切实际,但读完这本书,我的心境生了变化。梦想看似天马行空,但如果不忘初心,一直朝它努力,总会成功的那一天的。”
“对,最后一句,再来一遍,越是最后,越是语要不疾不徐,不要让听众、评委觉得,你想早点下台的感觉,慢慢的,可是慢不是基本忘词的感觉,看我说一遍,”笑笑老师做着今天最后的指导,“梦想看似天马行空,但如果不忘初心,一直朝它努力,总会成功的那一天的。”
下课了。
陈雨一直没回话,陈晴当然不知道,陈雨在和李大夫艰难对话。
笑笑老师接下来还有课,只在门口和陈晴匆匆交代几句,“陈老师,壮壮,没问题的!天天有进步!”笑笑老师厚厚的齐刘海像一丛草,他的眼睛里闪烁职业性的礼貌。
“我在门口听着,还是觉得他有些片段不稳。太贪玩了,在家练习有限,自我要求不高。”陈晴精益求精,说出担心。
“难免的,还是孩子嘛,陈老师教这么多年小学,比我有经验,是不是在学校对学生耐心可以,轮到自家孩子就忍不了了?”笑笑老师笑着,他招呼着门口认识的家长,“嗨,萌萌妈妈!嗨,葛翔爸爸!噢,招生处在右边,对,第二间。”
“和笑笑老师说再见!”陈晴见后面的学生已经等着进教室,抓着壮壮的小手离开“回”字,她捏捏壮壮,递上生鲜市买的饮料、点心,走近电梯时,忽然夸了壮壮一句,“真是妈妈的骄傲,妈妈的乖儿子。”
壮壮吸溜着吸管,拿着蝴蝶酥,不明所以,模模糊糊回妈妈,“我也爱你,妈妈。”
公交复公交,又是穿城而过,一小时后,陈晴带着壮壮抵达平和花园父母家。父亲陈抗美已被堂弟大强送回潞城,父母家和陈晴的小家住对面楼,平时的打扫、维护,两只猫的喂食、清洁都是孙大力做的。
壮壮跟在陈晴身后,来到姥爷家门口,只见妈妈还不时地翻看手机,不时焦躁跺脚,他差点被亲妈跺到,“妈!你干嘛呐!”小伙子不乐意了。
陈晴在电子门锁上按下九个数字,出九声滴,再按一个“#”,“您输入的密码有误。”陈晴想着待会儿要单独和爸爸面对,不免要交代孙大力行踪,不知道该不该如实说妈妈的病,心烦意乱。
她被壮壮一把推开,“你会不会啊?”小伙子在门锁上操作起来,正确的数字还没输入完,滴滴滴只滴了三声,门从里面开了。不是小偷,是陈晴的堂弟媳妇儿付霞。
“大姊!”付霞嘴角一咧,露出一朵笑,绿江喊姐都叫“姊”。
付霞长得像一扇门,她的脸是方的,单眼皮,薄嘴唇,个儿高、骨架大,身体单薄,皮肤黄偏黑,头反过来,黑偏黄。付霞穿一件黑白条纹T恤,短袖的边滚着一圈蕾丝。条纹T恤外,套了一条围裙,围裙上书两个大字:“厨神”。她的手上、围裙上都沾着面粉,一看就正在干活。
陈晴一愣,她让大强送父亲回潞城,没想到弟妹一起来了,会不会一大家子都来了?陈晴心一沉,陈抗美在老家花了多少,她管不着,陈抗美只要把老家人带到潞城,就是他们的招待任务,哪次不吃喝拿陪玩一整套,劳民伤财?孙大力不在,怕不是这次重担,要她一个人扛?
陈晴眼尖,瞬间已认出付霞的T恤是三年前,她进行衣柜革命,更新换代时,更掉的。这些年来,绿江的亲戚们还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习惯,爱捡城里陈家一家老小的旧衣服穿。尤其陈晴,大部分衣服淘汰时,都保持着九成新的品质,一些连吊牌都没拆。每次陈晴更新完衣柜,便用个大收纳袋装了,扔给6援朝,只等下一次回家探亲或绿江有人来访,捎回去分了。
“付霞来啦!”陈晴用三秒完成对付霞的上下打量,努出笑,“壮壮,”她回头招呼儿子叫人,“喊舅妈!”
“舅妈!”壮壮肉乎乎的脸蛋像历史上某个昏庸的儿皇帝,“好香!”壮壮吸吸鼻子,情不自禁道。十岁的他,是闻嘛嘛香,吃嘛嘛香的年纪,他刚吃完俩蝴蝶酥,喝了杯橙子味儿汽水又饿了。
他瞅瞅付霞,“舅妈,什么东西这么香?”付霞面对壮壮,比对着陈晴时,少了些局促,“刚炸的韭菜盒子,饿不饿?我给你拿一个。”她的声音飘荡在壮壮身后,壮壮已将双肩书包的肩带一脱,包“哐”卸在地上,穿着球鞋冲进厨房。
“壮壮,你穿着鞋在家里跑什么!”陈晴皱着眉毛喊到,可她的吆喝显然是白吆喝,她歪着身子,贝壳般柔嫩耳垂上的白金镶钻耳钉一闪一闪,付霞比陈晴小几岁,后天保养加天资,加工作性质,付霞看起来比陈晴大,而粗糙。
陈晴心事重重,脱高跟鞋的动作慢悠悠,她看见鞋架上,男人、女人、孩子的鞋,足足多了好几双,挤得她的拖鞋无处觅踪迹,一丝不快,悄悄爬上她的脸。
等陈晴在鞋架二层的最里面找到自个儿的拖鞋,她套上鞋,“哒哒哒”,拖鞋每挪移一步,都拖着尾音,客厅空荡荡,陈晴伸头看看厨房,厨房一地都是大强一家送陈抗美回潞城,随车带来的绿江的土特产。沾着泥土的荸荠、今天早上菜市场买的藕、半扇猪肉带着干涸的血,一桶绿江特产的茶树油。
灶台上则铺满了付霞做面食的家伙事儿,面粉、面板、擀面杖,搪瓷盆里拌着一整盆韭菜鸡蛋馅儿,捏成大饺子状的韭菜盒子,一些在面板上安静呆着,一些在锅里接受油与火的考验,一些已经出锅呈叠呈摞,搁在洗菜篮里,付霞跟着壮壮进的厨房,她拿起筷子和小盘,从洗菜盆里,夹出一个,给壮壮先尝。
“搁篮子里,不脏吗?”陈晴站在厨房门口眺望着,眉毛立着,点评着。
“大姊,篮子,我洗过了。”付霞轻轻答。
“哦。”
陈晴敷衍地回答,几乎像打。她提拉着拖鞋,在家转了一圈。她看到阳台上,一并打开三个行李箱,洗衣机在工作,出咔嚓轱辘的声音,客卧的床铺已经铺好。零七碎八的东西,如水红色的塑料口杯,卷了毛的牙刷,僵硬的毛巾若干条,已在洗手间水池前一字摆开……
看样子,大强一家都来了,要在潞城住一段时间,盲猜一下吧,暑假不完,大强家的娃、陈大路是不会走的,一如小时候,每年寒暑假,大强就像长在自己家。
顺便提一句,侄孙陈大路喊陈晴的爹、孙陈壮飞的亲姥爷、陈抗美,“爷爷!”
听起来,像亲孙子。
重男轻女害死人!
陈晴的粉色指甲,重重拉阳台门时,蹭掉了一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