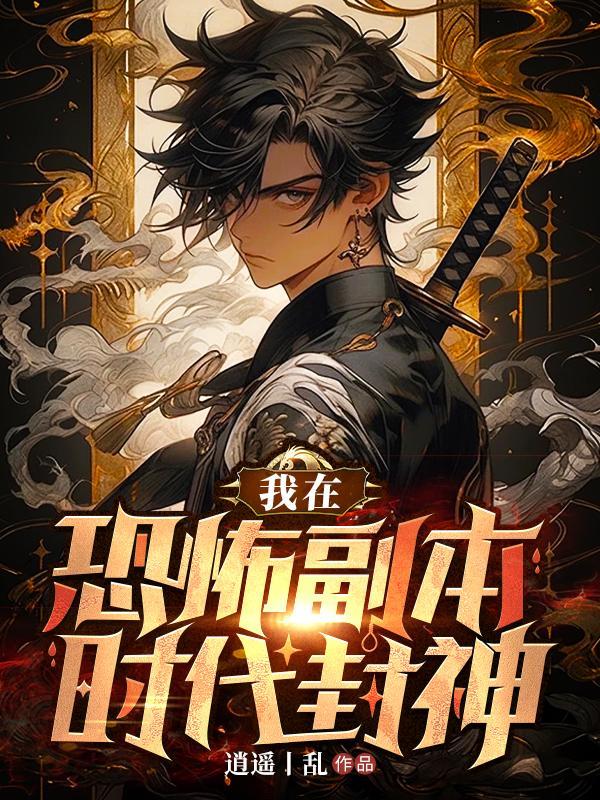风云小说>寻龙天师风铃里是啥 > 第127章 马王爷(第2页)
第127章 马王爷(第2页)
“马王爷,盗墓贼的恶咒……”
鹞子哥轻叹道:“多少土夫子在这上面栽了跟头,最后人不人鬼不鬼的死在了犄角旮旯里,搁旧社会,人们都以为是闹了瘟疫,就连亲爹妈都不敢给收尸,只能是往身上扔点柴火棍子,一把火就烧了。”
这种怪病。
鹞子哥还真见过。
病因,就来自于墓中出来的贴身随葬品上。
有人盗了墓,带出了墓里的明器,然后就染上了这种病,其实不传染,谁碰了明器,谁就会得这种病。
起初的时候是起类似于小哲别身上的这种脓包,慢慢的脓包烂开,浑身上下皮开肉绽,不疼,只是痒,痒的让人忍不住抓,一抓就抓下一层皮肉,许多人害了这病以后,都是活生生把自己给挠死的,有些心硬的,忍不住干脆直接自杀了。
民间老是说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这种病的脓疮看起来又像是一颗颗的大眼珠子,所以大家伙儿就叫做这种病是马王爷,得了这种病的人还给起了一个特贴切的名字,叫鬼眼佛。
你说说,这鬼眼睛里的佛,那还叫佛吗?只怕是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大仇人,人们只说大佛度鬼,却不想想这佛要是度不了鬼,反落在人家手里会是个什么下场……
鬼眼佛这名儿也准确,大概就是说,这是鬼神最凶狠的手段了。
我想了想,就说道:“你说,是不是明器上面沾染着一些霉菌之类的东西?”
“应该不是。”
鹞子哥说道:“如果上面果真有霉菌,那应该是碰了明器以后立马就得中招,可是这种病……作时间却不一定!”
他耐着性子解释了一下,说得了这种怪病的土夫子不少,有的是碰了这明器以后立马中了招,可还有一个,之前从一座大墓里取了不少金叶子,后来因为前面太凶险,便退了出来,那几片金叶子在他手里搁了好几年都没事儿,不过他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那座墓,后来邀了几位好朋友,再次下去了,结果还是没走远,破不开里面的一道墓门,只能退了出来,随行的两个好朋友都死在里面了,什么都没捞着,等他出来,再次把玩这金叶子的时候,就得了这种怪病,没撑多久就死了。
“说来说去,还有可能是霉菌,你不是说了吗,生这种怪病的,都是拿了人家贴身随葬品。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这种霉菌就是人家正主儿死后身上养出来的,附着在明器上,什么时候作,那就看正主儿的意思了。”
老白说道:“我以前就听过这么个说法,类似于摸金校尉这些专业的土夫子,把下墓看成是一场和鬼神的博弈,破开机关什么的,这是和正主儿较劲,你要赢了,理应有所得,所以,可以适当的带走一些东西,至于带什么,带多少,这都要问问墓主人了,仪式不像是大家口口相传的那样,人点烛鬼吹灯,实际要复杂很多,可具体怎么回事儿,这就是人家的不传之秘了,能和鬼神直接交流,这种手段也不可能喝多了就大嘴巴说出来,他们这么干,好像就是防这一手!
要我说,你那朋友就是太贪了!
之前他能拿到金叶子,那是人家正主儿不想和他计较,没成想他又杀了个回马枪,惹毛了人家,所以人家干脆就要他的命!”
这说法倒是也挺新奇,不过鹞子哥却不置可否,只是摇了摇头,说这种事儿他也不大清楚,反正他要下墓,墓里有正主儿,直接挑翻了,以绝后患,这样最安全。
“说来说去,也不是现下盗了墓就遭殃吧?”
我再次询问一句,得了鹞子哥的肯定,这才点了点头,心想他可能真冤枉了小哲别,对方刚死了儿子,眼皮子底下肯定没什么财的心思了,要说去盗墓,还真有点说不过去。
我略一沉吟,就询问小哲别:“大哥,以前你有没有盗过墓?你就放宽心和我们说,我们只管鬼神之事,不问人间之事。”
“小兄弟,信我一句,我真没盗墓,现在没盗墓,以前更没盗墓!”
小哲别苦笑道:“方才这位大兄弟也说了,那得是碰了明器的人才会得这种怪病,不传染,可现在大半个村子都得了这病,我们总不能全都盗墓去吧?说实话,要不是现在生活不易,我们都不可能进山去打点野货,以前都是本本分分的牧民。”
这话我信。
现在这年月,活着都不易,各自有各自的苦。
我叹了口气,话说到这份上,我信了他几分,再聊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但我很肯定,这牧区里,一定有一件明器,而且是大家都能接触到的明器!!
否则,不可能一下子撂倒这么多人。
我本能的想到了牧区里圣山的传说,难不成,所谓圣山,实际上里面是有墓葬,有人曾经从墓葬里带出了东西?
不管怎样,这件东西一定在公共区域里,供大家一起使唤。
当下,我站起身来,招呼了七爷准备出去瞧瞧。
不过,离开前夕,我的目光却落在了小哲别的床上。
准确的说,我的目光是落在了床上的枕头上面!
这枕头被枕巾盖着,不过看起来又长又窄,而且很高,十分怪异,咋看都他娘的不像是个枕头。
“稍微等一等!”
我看小哲别和他媳妇又准备回床上躺着,便立即叫住了二人,两步并作一步朝那枕头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