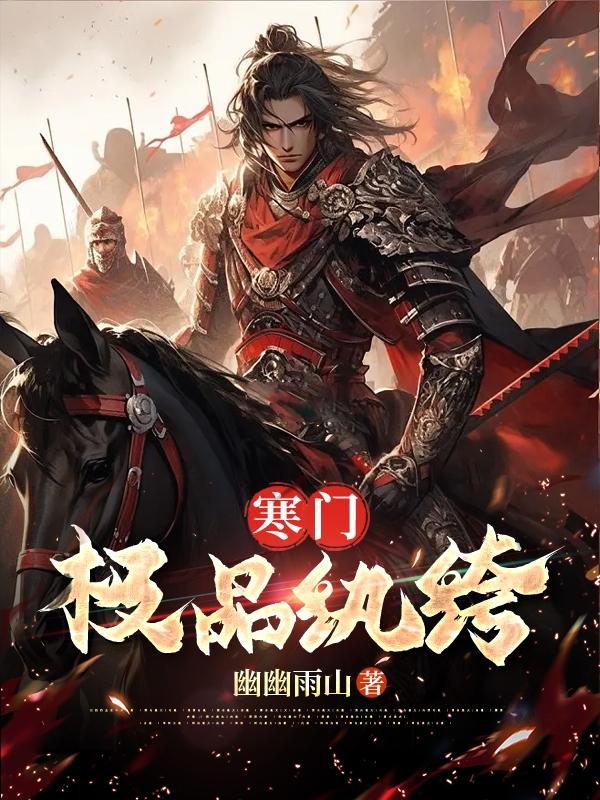风云小说>美人鱼存在吗 > 分卷阅读1(第2页)
分卷阅读1(第2页)
直到颜真谊在病房门口轻轻叫了一声,贺既明才放下手中的书。颜真谊走近后现许青蓝伏在病床里侧,睡着了。
贺既明没有话要和颜真谊说,颜真谊只能碍眼地站在一旁注视着沉睡的许青蓝。
贺越把手中的文件递给父亲,贺既明翻开后指了指修改的地方。两人交谈的时候贺既明的右手会轻轻摩挲许青蓝的脖颈,梢。
许青蓝过了一会儿像是被打扰般醒来,在见到颜真谊后不敢置信地唤他:
“真谊?”
“你怎么回来了?一切还顺利吗?”
“后面的巡演我想改几个动作,拿不准主意。”
许青蓝起身的时候颜真谊才现老师被拷在病床旁,贺既明旁若无人地拿出钥匙给他解开手铐,示意他们去里间交谈。
颜真谊靠在许青蓝身边,老师的味道很安宁,对他来说这是趋近于“家”的气味。
许青蓝没有错过任何一场演出后的录像与报道,自然也找到了他许多错处,数落起他。
他看着许青蓝板起的脸,却笑得像个小孩。真奇怪,幼时的他明明那么害怕许青蓝的严厉。
“你会来吗?最后一场。”
面对他的央求,许青蓝点头。
离开时颜真谊对着贺既明说再见,贺既明接着翻开那本书。
“我和你说过的话,别忘了。”
颜真谊的手一怔,随后干脆利落合上的门替他回答了贺既明。他没来由的想,如果贺既明想抹去他的痕迹,他该把贺家烧了才对。
家是回不去了,反正明天就要飞走,这一夜他可以随便找个酒店对付一下。
只是贺越不允许,因为家里的地板被他弄脏了还没有收拾。
“吴妈呢?”
贺越在车上面无表情地回答他,“回老家去了。”
进了客厅后他之前带进来的雪已经融化成了一长串的水迹,颜真谊叹了口气熟门熟路地去工具房拿东西。
贺越坐在沙上接到宋宁的电话,宋宁因为长病假休学了很久,如今正在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他和宋宁从小有着婚约,婚期正在计划中。
“嗯,按时吃药我会检查。”
他一边打着电话一边看颜真谊擦地,颜真谊没有拿拖把应付了事,尽管他的腿上了巨额保险,不应该于此刻跪在这里。
他听见贺越的手机中传来宋宁的笑声,也许是在撒娇,最终得到了贺越的那句“我也想你”。
随后一双手攀上贺越的小腿,覆上膝盖。
贺越俯视着地上的人,他有一张极其清纯的脸,报纸上说他像初生的天鹅,但撰写新闻的人应该没想到这只天鹅喜欢做淫荡的事情,比如勾引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
他冷着脸起身,嘴边还在回应着宋宁日常的询问。
——吃了什么,做了什么,见了什么人。
而颜真谊攥着他的裤脚不让他移动半步。
当然,贺越可以推开他或者一脚踹开,颜真谊单薄得像张纸,这很容易做到,就像一年前那样。
但此刻贺越应该静悄悄的,是的,他不该挣扎惊扰到宋宁,这才让颜真谊有机可乘。
身下的人颤颤巍巍地解开裤子,贺越握着手机低头看他伸出舌尖舔舐,疲软的阴茎没多久就变得狰狞。
期间颜真谊抬头看他,眼神倒还是一副纯真的模样。温暖的口腔,牙齿熟练地隐藏了起来,欢场老手,这张嘴也不知多少人享用过。
他们在电话中谈论天气,宋宁听闻崇市下了大雪吵着说要回来堆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