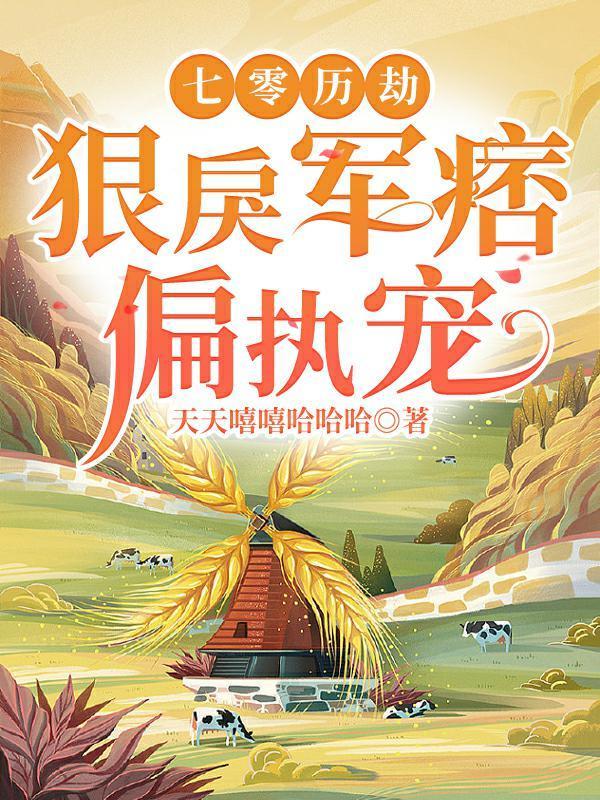风云小说>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图片 > 第36章 王爷的白月光(第4页)
第36章 王爷的白月光(第4页)
她看着文弱,却不是轻易认输的人。但有些话闺阁女孩不好说,只好撺掇姐姐来说。
萧云画羞赧一笑,“姐姐怪会说笑,当着人家齐王妃在这里,怎好说这些。”
立马将萧云舒的火拱出来,当着齐王妃更要说,能气死她最好。
故而挑起眉眼,“欸,齐王妃又不是外人,实话实说罢了。幼时齐王确实打算与你结成夫妻呀。”
确实有那么一桩事,却不是齐王的意思。
那时萧云画年纪小,皇后说等她过了及笄再婚配李辞。待她满了十五岁,没多久李辞出意外成了废人。
这段婚事如同断线风筝远去,皇上与皇后不再提起,就连当初极力促成这段婚姻的萧大将军也按住不表。
如今旧事如同旧疮疤,萧云画以为已经结痂长出新肉,蓦地被齐王妃一抠,鲜血直流。
她才觉伤疤并未好全。提起李辞二字,便有绵绵的痛感钻入骨头缝里去。
萧云画些微偏头,笑得苦涩,“小时候过家家的事情,哪里作数。”
絮儿心底呵呵,你们小时候玩的最好是正经过家家。以她丰富的过家家经验,小屁孩在一起玩八成要扮爸爸妈妈。
而她通常在孩子堆里演那个生病,饿肚子,不做功课的傻孩子,被和她一般高的“爸妈”照顾或者教训。
絮儿喝茶压火,慢悠悠扇风,显出十二分的大度,“也是,云画小姐才貌双全,世上有的是美男子相配,我们王爷没那个福分。”
本来就是,且不说李辞毁容落下残疾,单那样古怪的性情,千万别祸害人家大美女。
絮儿撇撇嘴,心道李辞不适合娶妻,只适合在床上独自烂臭。
见絮儿满不在乎的样子,萧云画心内愈酸楚。在她心里,没福分的那个人显然是她。
她的整个少女时期都在暗恋李辞中度过。与其说是青梅竹马,不如说是她一厢情愿。
李辞出事后,父母兄长劝她不必再等,为她挑选了好些才貌双全的官贵公子。
侯门公子,她嫌仰仗祖辈的男人没能耐;新科状元,她嫌人家上赶着巴结没诚意;军中红人,她嫌行伍出身煞气重。
横竖哪里都不如意,迟迟不肯点头。如今眼见快守到十八,不知道在守什么。
萧云画骤然收回神思,垂头极轻地叹了句,“他怎么样都是最好的。”
抬眼再瞧絮儿,美是美的,却与李辞不匹配。在她心中,李辞简直举世无双。
连自己也是堪堪可配。
没曾想,贵妃娘娘给他找了个商贾人家的女儿匆匆成婚。听谈吐,没怎样读过诗书。论气度,似乎有那么一些俗。
她替李辞万分不值。
不经意地就从嘴角溜出些嘲讽,“聊了这样久,还不知齐王妃叫什么名字?”
她知道齐王妃叫白絮儿,明知故问。
絮儿只当她热情,没多想,剥了葡萄皮拍拍手,“我叫白絮儿,就是白色的柳絮飞飞飞。没出处,出处可能就是一棵柳树。”
说得萧云画掩着纨扇笑,笑里掺着些别扭的恨。恨不能化作是她,等会儿就能跟着齐王府的马车回去见李辞。
絮儿也觉得和萧家姐妹聊不到一处。一个粗蛮泼辣,一个高洁文雅。她横在两个极端中间,坐立难安。没说几句就辞别回家。
萧云舒懒得送她,倒是萧云画热情地送她到门上,“我跟着母亲回京得有半年,不喜欢在家枯坐,总往姐姐这边。齐王妃常来玩。”
絮儿笑呵呵点头,她哪里敢再来。燕王府简直是龙潭虎穴。一个李赟总色迷迷地缠着她,一个萧云舒总恶狠狠地瞪着她,如今又来个萧云画,还是自己男人的白月光。
乱,太乱。
此时集美来报车已修好,絮儿匆匆辞别萧云画。来至角门,刚要打帘子上马车,又见她追上来,“王妃留步。这本书是珍本,前些年辞哥哥托我找的,劳你带去给他。”
絮儿客气接过瞟一眼,连书名都不认得。
暗暗咋舌,她一个正妻给他们跑腿送定情信物?这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