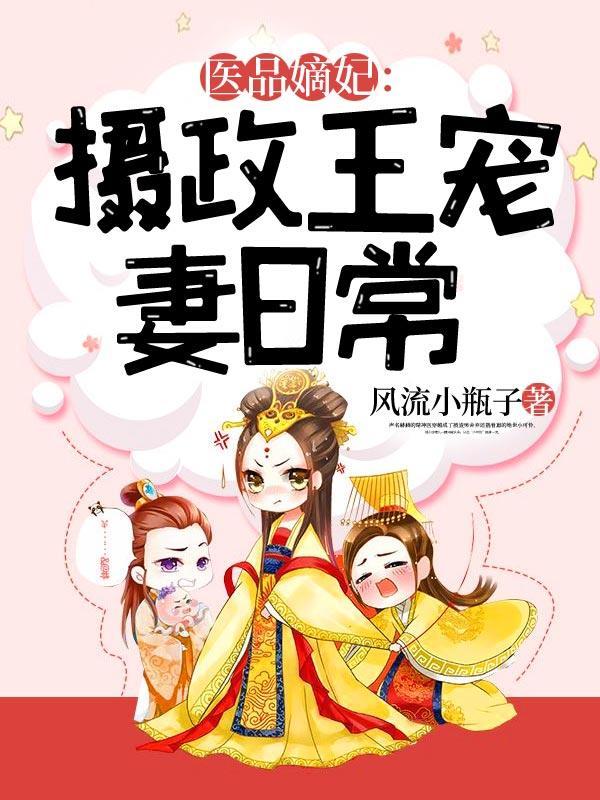风云小说>地表最炸cp宝书网 > 第94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程咬金母子重逢(第1页)
第94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程咬金母子重逢(第1页)
话说公主在营帐里正要入睡,忽然闯进来一名男子,并且倒头就躺,还对自己动手动脚。公主定睛一看,只见来人正是她心心念念的孔京。不知怎么的,她忽然停了反抗,似乎只要是这人,怎样都好。
孔京在一片迷迷糊糊中,双手用力,似乎抓到什么。他心知,要是过头,娘子早抱怨了。至今没吭声,那就是默许的意思。
这番动作中,公主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人竟然那么胡来,也不问她一声。她又想起孔京常做的动作,一拧脖,嘴硬道,“老子就是要造反!你能咋的?!”哼,这人就是胡来!他要是不胡来,就不是他了!
喜的是,这人竟然对自己胡来了!虽然她很讨厌这人的粗鲁,尤其是那一口一个“老子”,跟这人那些响马手下一样,疯狂极了。如今,他甚至疯狂到,钻地底下来寻什么宝,神经病!
可是,不知为何,自己心底竟然隐隐有种期盼,渴望这人对自己胡来。也许,这人实在太俊,长得太讨自己欢心。也许,他胡来够了,受自己感化,没准就不疯,不造反了,老实跟自己回京去,向父皇讨个官做,从此过安生日子。
冥冥中,她感到那只大手,力道越来越大。她低声抱怨,“疼,疼。”仓促中,她感到呼吸困难。一种陌生的感觉随着大手的动作,如同波涛般一阵阵传来,令她的心就像飘在大海上的一叶扁舟,时起时落。
可惜,她抱怨什么,孔京完全听不到。为了躲避身边喋喋不休的怪影,孔京早已用布把双耳堵住了。现在,他只感觉,娘子的傲人物事似乎变小了。大概是错觉,这物事只会越来越大,怎么会变小呢?不科学!
黑暗中,营帐里似乎进了一条蛇,或是别的什么东西。这地窟里稀奇古怪的东西太多,就连长得怪模怪样的蛇,公主也都见过好几次,周围人还抓了烤来吃。天哪,那怪模怪样,张牙舞爪的小东西,看着就令人反胃,亏他们吃得下去!
她想叫,“有蛇!”可是刚开口,一张柔软的物事就贴了上来,如同芬芳四溢的蜜壶一样,令她陶醉,浑身的力气似乎都没了。
孔京渐感无聊,过去一贯是娘子主动,要这要那的。今天不知是吃多了,还是走累了,睡得跟一段木头似的,很无趣。不过,就算不说话,孔京也知道娘子喜欢什么。
一番折腾闹出不小动静,孔京堵上耳听不到,倒是惊动了营帐外的人。紫妍过来好一阵了,同站岗侍卫们唠了好一阵家常。他们虽然是公主的人,但跟着夫君一路走来,也有一个多月,早混熟了。听到这声喊叫,这几人一齐回头望向帐内,笑得龌龊。
紫妍心想,夫君终于收了公主了。这天,她早料到了。即使还没名分,公主迟早是夫君的人。所以刚才,她得知夫君误进了公主的营帐,并没冲进去打扰。因为她早知道,这都是迟早的事。就跟百川入海,日出日落一样平常,哪里是她管得了的。
这时,眼前晃动一条倩影,有人带着哭腔,走到她身边,喊着,“姐~~~~”她定睛一看,来人正是自己拜把子的妹妹,单盈盈。
盈盈没听到公主的惊呼,她现在只有自己的心事。紫妍转头,柔声问道,“妹,怎么了?”她胸大心也大,或许是心宽体胖的道理。平时妹妹有啥心事,都爱同她说。
只见她拉着紫妍的衣袖,抽抽噎噎地道,“那人,那人他打我。我害怕,不想见到他。”紫妍想起不久前同罗成对打的那一幕。当时罗成明显神志不清,或许是受周围古怪的蘑菇影响。她揽住哭泣的盈盈,柔声安慰道,“别气了,那是事故,他也不是有心的。”
“他,他狼心狗肺!我见他伤得厉害,好心帮他包扎换药。他倒好,伤好一点,就同我哥打架!”盈盈越说越气,眼泪哗啦啦就下来了。“今天,他还打我!还打我!”
紫妍看着自己这妹妹哭诉,心里也不是滋味。自己同罗成对打过几次,对他的能耐有数。相处也有一月多了,对他的为人也有数——这少保哥仗着爹是朝廷重臣,根本不把别人放眼里,鼻孔都冲天开,还成天一脸“你们这些响马都是贱民”的不屑。
要不是夫君倚重罗成,再加上亲戚关系,自己绝不会给他好脸色。紫妍于是宽慰道,“妹妹不服,可以跟我一样,打回去呀!”
盈盈摇头,嘟着嘴道,“我,我舍不得!姐,你帮我揍他一顿,如何?”紫妍摇头,“我打不过他。”废话,论拳头本事,这里怕是没人打得过罗成。盈盈又道,“也不用真打,就轻轻,轻轻教训他一下就好。”接着,又补句,“别打疼了。”
这下,紫妍算是看明白了,这俩是冤家,管不了啊管不了。她于是闭嘴,抱住盈盈,反正哭累了,该咋咋的。这时,有人轻手轻脚地走近来,劈头就问,“孔公子呢?”借着火光,周围人看到,来人正是袭人。
紫妍冲营帐里努努嘴,正好里面传来低沉的喘气声。袭人心领神会,望向旁边营帐,低声道,“奴家今夜在这里歇好了。”紫妍点头道,“等等我。”
多日来,几名女子有了默契,晚上要一同睡。毕竟周围这些汉子是干响马的,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麻烦。今晚,紫妍少有的没缠夫君,她拉着盈盈走向旁边营帐,还嘱咐侍卫道,“别偷看,也别给人进去。”
第二日清晨,不知什么时辰,孔京终于醒了。昨晚折腾得厉害,累惨了,于是一觉睡到现在。他刚睁眼,就看见枕边有个女子,长飘飘如同瀑布,一直垂到自己胸前。奇怪,娘子的头,什么时候这么长了?
“你醒了。”女子朱唇翻动,吐出句话来,却不是娘子那熟悉的声音。孔京晃晃头,定睛一看,顿时吓一跳。眼前的女子,哪里是他娘子,竟然是他多日来厌烦的公主!而且,不着寸褛!
他一个激灵,跳起来嚷道,“你,你怎么在这里?”
公主皱眉,反问道,“本宫才想问,你怎么在这。”孔京忽然想起,这番对话似乎见过。那都是一月多前的事了,初遇没多久,他也走错过营帐,与娘子一同睡在公主的帐里。
不过,这次同上次有点不一样,他忽然感觉某个部位凉飕飕的。而且,自己还有了年轻人都有的起床反应。他低头一看,心里一惊:咦,小弟上怎么有血迹?受伤了么?怎么自己都不知道?
公主看着孔京的这番动作,有点想笑。这人昨晚干了什么,自己都不知道么?这时,孔京抬头望向她,四目以对,只听他辩驳道,“我,我睡糊涂了,以为是娘子!”公主嗯了一声,似乎在说,无所谓了,现在本宫也是你娘子了。
孔京万万想不到,自己在迷迷糊糊中竟然同这聒噪的女子缠上了。天哪,看着这些血迹,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他望向公主,道,“昨晚,我都干了什么?”公主媚眼如丝,反问道,“你自己都不知道么?”
“我,我累糊涂了,怎么不叫醒我?”公主皱眉,想道,本宫为什么要叫醒你?又感觉这么说,好贱。话到嘴边,变成另一句,“你疯,本宫拗不过你。”然后又补了一句,“反正,本宫是你的人了。”
正是:
誓死不嫁无情汉,偏生情郎硬上弓
欲拒还迎谁解意,生米煮成熟饭来
然后,两人尴尬起来,相对无言,最后是公主打破沉寂,道,“本宫感觉背上怪怪的,你来看看呗。”孔京本想吐槽道,你皮痒关我什么事?又想到昨晚的事,只得凑上前。
只见公主转身,现出莹白如玉的颈项,如同一卷美轮美奂的仕女画卷。孔京不由伸手,轻抚了两下,低声道,“哪里痒?”公主打个哆嗦,低声道,“你看有什么古怪?”
孔京连看了几遍,才道,“真没什么古怪。”他忽然想起,一月多前初遇时,他看到公主背后有个古怪的咒纹。徐茂公还说,这是“生死结”。如今,这东西似乎长了脚,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他下意识地举手,现自己手心的咒纹,一同消失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昨晚自己对公主做的事,破了咒纹?孔京心里乱了,要是徐茂公或淳风小弟在身边就好了,还有个人问问。如今,他和公主只能对望,大眼瞪小眼。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正在两人在地底纠结时,距离此处一百多里的地方,程咬金和王伯当两人走了三天,终于来到程咬金的祖屋了。这里,是乡野里的一处僻静所在,小小茅屋坐落在山脚下,似乎是附近村子的一部分。不知为何,这里同周围人家隔了老远,即便有人进出,村里人也不会知道。总之,是被孤立了。
来到屋前,程咬金一把推开门,大叫,“娘!娘!”无人应答,只有他的粗嗓门回荡在周围。一群鸡鸭在院里到处乱窜,明显有人居住。程咬金脚快,转眼间就把屋子绕了遍,硬是没见到他娘。王伯当跟在他身后,忍不住道,“家母怕是出去了,稍等便是。”
程咬金点点头,这里他都快两年没回来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记得还带了尤俊达一起来,把娘乐呵的,捣鼓了一大桌好吃的。之后,尤俊达带着他东躲西藏,躲避官差的追缉,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也没想起给娘捎个信。如今好不容易在瓦岗山上安了家,他一定要带娘同去过好日子,孝敬他娘。
这一等,就是大半日。直到日头西垂,才有个中年大娘姗姗来迟。只见大娘一身农家打扮,穿着十分简朴,显然没装扮。她刚进家门,程咬金抬腿就跪,喊道,“娘!孩儿回来了!”大娘扶起他,满面笑容地左看右看,喜道,“哎哟,看看,这不是我的阿牛么?阿牛回来了!”然后,母子俩一番唠叨,看得旁边的王伯当有点感动。
晚上,程咬金同妈叙旧后,叫妈跟自己上山享福去。他说起自己在瓦岗山上的兄弟,又是好一番吹嘘。大娘虽然舍不得祖屋,然而丈夫死得早,程咬金的弟妹们命薄,又都先去了,只剩他这独苗。大娘本想守屋,无奈晚年寂寞。在程咬金一番力劝后,才勉强答应下来。
隔日,大娘带上些细软,就跟着儿子和王伯当,踏上去瓦岗山的回程。这个家自从亡夫走后,就日渐破败,确实也没什么值得留念的。他们走前,王伯当在后,心想这一路还蛮顺利的。这四哥毛毛躁躁的,原本自己担心会出什么事,怕是多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