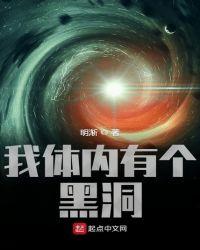风云小说>贪欢 > 24 第二十四章 容我放肆一回(第4页)
24 第二十四章 容我放肆一回(第4页)
司湛看司洸形似癫狂,不解他为何能生气至此。
司湛来时见到了在万蝶园等司洸的周姑娘,仔细想想,大概司洸的心上人在等他的答复,太子妃没有定下,纳侧妃更是遥遥无期,司洸难免心情急躁。
听司洸问他缘由,司湛没有隐瞒,直言道:“我十岁之时,父皇命杨阁老教我写文,我常去杨家叨扰。那年大雪纷飞时,我见到了穿着海棠色夹袄的江二姑娘。我那时身体还未大好,时常咳嗽,七岁的她端着一碗冰糖雪梨进来,‘小哥哥,你可要尝尝,我之前咳嗽得厉害,喝这个便好了’。”
司湛说起来,想起那时她双眼盈盈若水,实在可爱。
“我没理她,她放下碗就走了。过了几日我去杨府时,发现我的书不见了,原来是江夫人委托杨阁老教江二姑娘学文,她在杨家书房里挑书,误把我看的书当做杨阁老的书给挑走了。”
“又过了半年,那本书回到了书房,她认真看了数遍,书页间夹着数张白纸,上面工整地写满了她看书时的不懂之处。她想等杨阁老有空时为她解答,恰好我有空,我便拿了宣纸,裁剪妥当,在纸上面一一将她的问题作答,再夹在对应的书页中。”
“杨阁老知晓之后,说他教我,我教他外孙女,他乐得偷闲。如此七年,我虽未再见过她,但她学文解字,是我所教。”
司湛浅笑,眸中流露出些许温柔,“因而我对她有所好感,也是人之常情吧,太子殿下。”
司洸听他娓娓道来,五内业火焚心。
原来司湛不是不近女色,而是一直惦记着他的妻子!
哪怕前生江神聆与他并无什么交集,司湛也从未与他道出过这些心思,但司湛的心里,也一定是念着江神聆的!
司湛装得清冷疏离,不爱与人打交道,去游历四海,去那些荒无人烟之地,北上冰河,南下海屿,也只是不想见到他和江神聆伉俪情深吧?
如今司湛有机会谋划娶江神聆为妻了,司湛拍起父皇的马屁,不也得心应手吗。
表面霁月风光,心里却一直爱着自己的嫂子,真是令他作呕。
司洸浑身血液叫嚣,眉眼间戾气丛生,“你……”
他们身后响起皇后的惊呼,“你做了什么?你打了湛儿?”
长街尽头候着宫女内侍,皇后快步走过来,她停在司湛面前,凤眸里尽是担忧。
司湛抬手遮住泛青的颧骨,“母后,我没事。”
皇后转头,愤懑地盯着司洸,胸腔起伏不定。
随即她一把抓住司洸的胳膊,“随本宫回凤栖宫!”
司洸眸底阴郁积压,母后拉他,他纹丝不动,定定地盯着司湛,“从此,便再没有兄弟之情了。”
言罢,他抽回母后抓着的胳膊,沉声道:“我也有些事情想与母后说。”
斜阳西照,三人的身影落在暗红的宫墙上。
风过,司洸宽袖的影在墙上飞扬起狰狞的弧度。
司湛锦袍窄袖,唯有衣摆轻轻飘起,落在墙上的阴影,挺拔笔直,似岿然不动的青竹。
司湛方才想,若司洸得知他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直心有所念,以己度人,应该能够体谅他的心情,收了脾气。
未曾想司洸得知之后,火气更盛。
他盯着母后与兄长离去的背影,“殿下,也心仪江二姑娘吗?”
***
凤栖宫。
夕阳西下,皇后仪仗停在宫门前,在凤栖宫的琉璃瓦上嬉戏的雀鸟扑簌簌惊飞。
皇后对刘嬷嬷说:“去给敖公公说一声,本宫和太子身体不适,晚宴便不去了。”
宫女推开八宝雕花槅门,皇后与太子沉默着,一前一后走进正殿。
皇后对宫女吩咐道:“你带着殿中所有人退到凤栖宫外。”
宫中人散尽,宫门沉重关上。
皇后当即从凤座上站起来,一巴掌甩在司洸脸上。
司洸的手搭在黄花梨木的扶手上,母后气冲冲地走过来时,他能躲,但他半掀眼皮,扬着头,将脸摆好,由得她打。
皇后的金玛瑙护甲尖锐,滑破了司洸的嘴皮,他舔了舔嘴角的血,腥甜的味道。
“解气了么?”司洸扬起另一边脸,“不小心伤到了你金尊玉贵的湛儿,没解气便再打。”
“母后打完了便说一声,我还有要事求母后相助。”
皇后捂着心口,被他气得头晕目眩,她回退两步坐在凤座上,“你到底在发什么疯?你想本宫和你弟弟跟你一起死吗!”
“放心。”司洸端起一旁的茶水,浅润干涸的唇,“父皇除掉先皇后和废太子的时候,把他成年的皇子杀了个干净。如今膝下只有二十六岁的鲁王,但那是个只会斗鸡狎妓的纨绔,我和瑾王都是母后所出,再有便是娘家出身及其低微、由母后养大的瑞王,他废了我,立谁?”
“若母后盼着父皇改立瑾王,那母后也依旧是皇子生母,又有何惧?”
司洸无所谓地笑了笑,“父皇已经不年轻了,不能像年轻之时,将看不顺眼的亲族杀个遍了。再杀,那他就后继无人了。”
皇后揉着胀痛的眉尾,冷哼道:“前朝显王的嫡长子,当了三十年太子被废,显王死前立三岁幼子继位。以史为鉴,你别以为如今只有你们几个皇子,你的位置便坐得稳当了。”
司洸眸色微暗,轻声点头道:“母后说得在理,是得先把威胁我的人给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