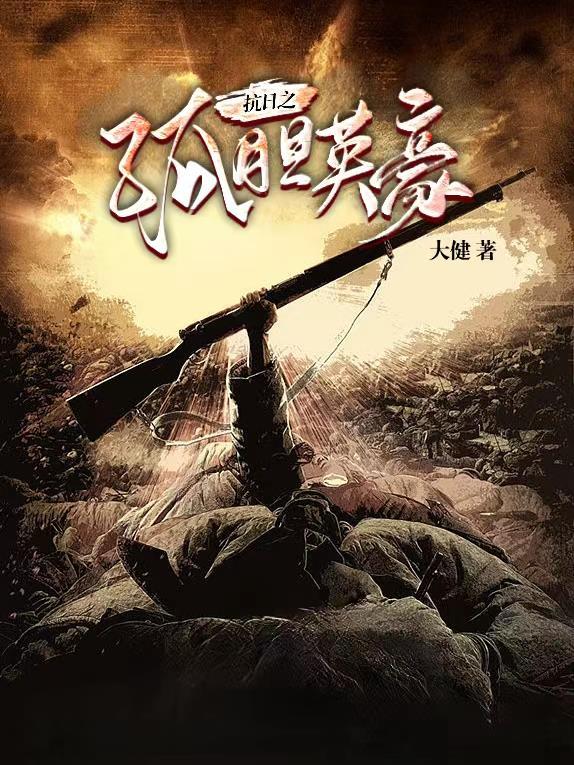风云小说>贞观长安小坊正txt > 第708章 作(第2页)
第708章 作(第2页)
范铮笑而不语,6甲生翻了个白眼:“老规矩,腿打折,扔武候铺。”
当然这奢侈的法子是没法推广了,连6甲生都不敢这么玩,只能隔三差五到侯府来偷菜。
法不责众,就体现在这里。
范鸣谦撅着嘴,跑过来告状,一脸委屈。
要知道,即使是去宣阳坊万年县衙,明府、赞府、少府都得和颜悦色,让6甲生坐于他们一旁呢。
至于说冷天没法种菜,那也不是绝对的,草棚搭起,披上厚实的白毡、毼布,内里早晚搭火炭盆子,一样能种一些蔬菜。
范铮笑了笑,拍拍6乙生的肩头,转身回侯府了。
范铮本人对花花草草也不太感兴趣,除了留一片让杜笙霞想种啥种啥,其他的也将就范老石了。
岁数大了,中风能及时救治,身体还是能慢慢恢复过来的。
范铮领着两个娃儿,慢条斯理走到菜地前:“大郎、二郎记住了,久病床前无孝子。即便府上不乏防閤,可哪个防閤能长期忍着恶心,照顾一个动弹不得的中风患者?”
范铮飞起一脚,踢到6甲生屁股上:“怎么说话呢?不盼着我点好?”
连姜茯苓本人都只是逮了两个倒霉蛋出气,没法再细究下去了。
&1t;divnettadv">本来同行就是冤家,太医署有酒精使用的消息,就足够让人觊觎了,你还真能把长安城的同行都抓了不成?
多少人奋斗了一辈子,还在“吏”或“流外官”的身份上裹足不前,6乙生就是管了一下本坊便能捞到官身,还有何奢求呢?
范铮呵呵一笑:“多大点事?6乙生随我奔波了几年,也该有一个官身了嘛。”
难怪那些世家千年不倒,原来是顶缸的人多啊!
范铮没细说的是,姜茯苓事件,涉及的不仅是太医署,种种迹象表明,许多药行、医馆都可能涉及。
范铮苦笑:“你以为世间的事,非黑即白?姜茯苓之事,确实弄倒了一批人,可哪里不都是跑了穿革履的、抓了穿草履的?”
说起功劳,6甲生面现得色。
候在坊门处,见到范铮骑着黄栗细马归来,6乙生的笑容,绽放得比娶亲那天还美。
在关中粮食普遍紧张的前提下,能让敦化酒坊继续造酒精,已经是朝廷最大的善意了,扩大规模的粮食,打哪儿来?
连元鸾的拧耳与老子蜀道山都没得作用了,可想而知,倔到了什么地步。
范铮下马,嫌弃地摆摆手:“收收味,多大一个将仕郎啊!6甲生那厮还是宣德郎了呢。”
6乙生恨恨地踢了一脚坊墙,不知道这一肚子气该咋撒。
对于家人的劝阻,范老石吹胡子瞪眼,咆哮如雷,连范鸣谦都被骂了两句。
6乙生恍然大悟。
“仅仅是病还行,若是连病带作,早晚有一天,屎尿拉犊鼻裈里都无人过问。”
扔给武候铺,则是给武候们一个功劳,相互示好,日后武候们对敦化坊之事也多上心一些。
看到6乙生忿忿不平的样子,6甲生飞了他屁股一腿:“瓜皮!要是有人攀咬到县侯,你不得挺身而出,先顶住再说?”
范老石的身体,自上次痊愈之后,体质差了许多,舞枪弄棒的事也只得停了。
范老石阴沉着脸,提着鹤嘴锄起身,望向范铮的眼色饱含着怒意。
“看来阿耶是恨不得给我一锄。”范铮眼里闪着恼火。“要不,伱给了这条命,还是赶紧取走,省得日后受你折磨。”
范老石闷哼一声,鹤嘴锄掷地,转身离开菜畦,回床躺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