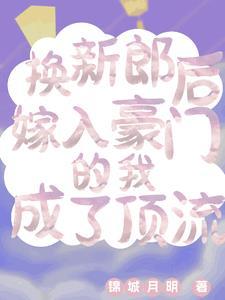风云小说>年代激荡1977 > 第27章 翻译唐璜(第2页)
第27章 翻译唐璜(第2页)
七十年代往后,纯粹钻研于国内文学的文坛作者渐渐增多,但从十年雨幕往前算,大凡真正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手上都有几部翻译作品:
比如季献临与金克木的梵文研学纠葛;
比如钱中输与杨降两位学界常青树;
再比如如今的文联名誉主席茅盾先生。
如果真能把《唐璜》这部具有代表性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翻译成功,“顾秋”就不止是谍战小说作家,更是译者顾秋。
这样一来,他的起点就会更高,且短暂弥补了尚未创作主流传统文学的缺憾。
“那就定在几天以后,这周末,我们一起去护城河!”
……
当日傍晚,聂子航坐在宿舍,翻阅着从杨降手上拿到的《唐璜》原本。
();() 如果从后世的眼光品评该作所有的中译本,无疑是查良争先生的翻译版本最为经典。
据传闻,当年查良争的妻子过世,查先生悲痛欲绝,在1972年之后开始翻译妻子最喜欢的英文诗歌。
《唐璜》就是其中之一。
可惜的是,因雨幕之故,该稿曾被三烧三废,直到1980年,查先生完成主体译作,带着未完成的遗憾离开人世。
有着这段丰富的经历,在译稿的水准与情感基础上,聂子航显然不能与查良争先生比肩。
但他可以从信、达、雅三方面,译出属于他的特色。
譬如拜伦的诗体韵律,与意大利八行体的格律诗十分相近,聂子航特地在图书馆找了部分同世纪的英文中译本做参考。
而拜伦在整篇《唐璜》中的口语体,以及立意中的讽刺艺术,都需要完全保留下来,这样才是一篇完整的《唐璜》。
有了翻译思路,也做足了准备工作,聂子航开始尝试着做初稿翻译:
“……我的心灵之翼垂落了,不再飞扬;
只有可悲的真理在我桌前缭绕;
把一度浪漫的事物都变为讥嘲。”
文字从笔端下方如流水般淌出,有了数十万字的《潜伏》做地基,他的文字素养确实提高了不少档次。
19世纪特有的浪漫主义哀愁口吻,也被他模仿的淋漓尽致。
一千字的篇幅,很快被聂子航翻译完毕,他满足地长舒了口气,精神清爽,仿佛洗了一个通透的热水澡。
聂子航拿起初稿,满意地审视了一遍。
——没错,是合拍的,而且是长镜头式的合拍。能做到这個程度,不仅需要丰富的语言功底,还需要一点未被磨灭的灵性。
除了部分西方专有事件、人物名词等仍须阅读其他文献进行校正,这篇初稿已经堪称完美。
傍晚的日色还未泯灭,夕阳还悬在窗底的一线天上。
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连那充满礼貌的敲门声也令他分外耳熟。
“请问,顾秋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