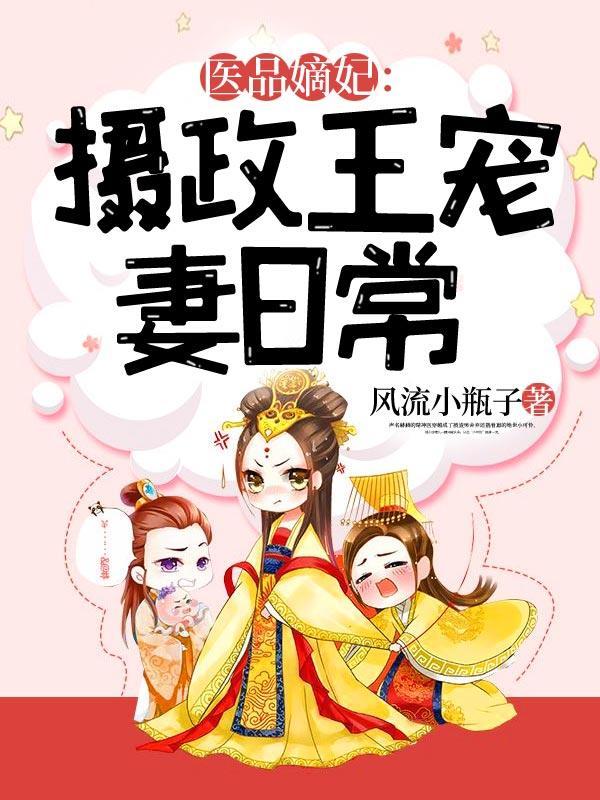风云小说>雨下一整晚吉他谱 > 第28頁(第1页)
第28頁(第1页)
她對所有東西都不抱期待,也很難失望。
況且,她從汀南出來本就是為了散心。
別的都是次要。
她補充說:「我比較隨緣。」
夜色深,戶戶燈光變暗,煙火氣散去,玉溪街道上的人越來越少了。好像一鍵點上關機,所有的一切都被黑色籠罩,唯有暗淡的路燈徹夜運作。
「那你呢?」話題都指著她,黎哩兀的轉移,反問他,「那麼功利的你怎麼從汀南跑到這兒了?」
攻擊性很強,她還不忘還以先前宋馭馳的「冒犯」。
宋馭馳掀起眼皮,懶散地也只是說:「曬太陽。」
汀南迎來颱風天,未來將會持續很長一段危險天氣。
前往玉溪過夏,是洗刷烏雲的過程,好像從糟糕的暴雨天氣走進晴朗好天。
他是這樣。
她又何嘗不是。
盛夏里,少年的氣息很燙。
他們靠近時,他那端的熱氣好像要將她皮膚灼燒,好想要一點一點將她溶解。晚風吹拂過來,黎哩才注意到他今天穿著白T,乾淨清爽的,不偏不倚少年時。
可少年那雙漆黑的眼底時常藏著一層霧氣,灰濛濛的,像堅硬的骨骼被鐵棍擊打,他低著頭,看起來又頹又喪。
肆意和頹敗兩種矛盾在他身上並存著,他看起來並不是很好。
黎哩不知道他經歷過什麼,但今晚,在這個時刻,她忽然好想撫平他皺起的眉。
她說:「宋馭馳,昨天的暴雨淋不濕今天的我們。」
所以啊,你要振作起來。
溫嫦以前說過宋馭馳,在她的形容詞裡,宋馭馳是個意氣風發,萬事順遂的少年。
在理想的國度里,他對生活永遠充滿敬畏心。
黎哩認識他很晚,不曾見過這般的他,但有那麼一瞬間,她忽然從心底希望風波平復,殺死苦難,希望他以後可以在生活里如魚得水。
疾風繞旗,希望他可以永遠這麼光鮮。
虎口和舌尖發麻,心臟跳得好快,心口好像有什麼東西要從胸腔里震出。隨著晚風,一下又一下。
黎哩有些慌亂地擰開瓶蓋,潮濕的鹽晶和微澀的琥珀泛著光,玉溪仲夏的第一個夜晚是鹹的。
瘋了,她應該是有點喜歡他。
溪邊野草生生不息,流水聲和蟬鳴此消彼長。
宋馭馳微眯著眼,雙眼皮褶皺處變深了一點,漆黑的瞳孔在暗夜下明亮又深邃。他目光灼灼地盯在黎哩臉上,怔愣片刻,他忽然歪頭輕笑了聲,「哪兒來的那麼多感慨啊?」
模樣有些痞,他懶懶散散的,不知道他有沒有聽進去。
她笑起來,又說:「隨便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