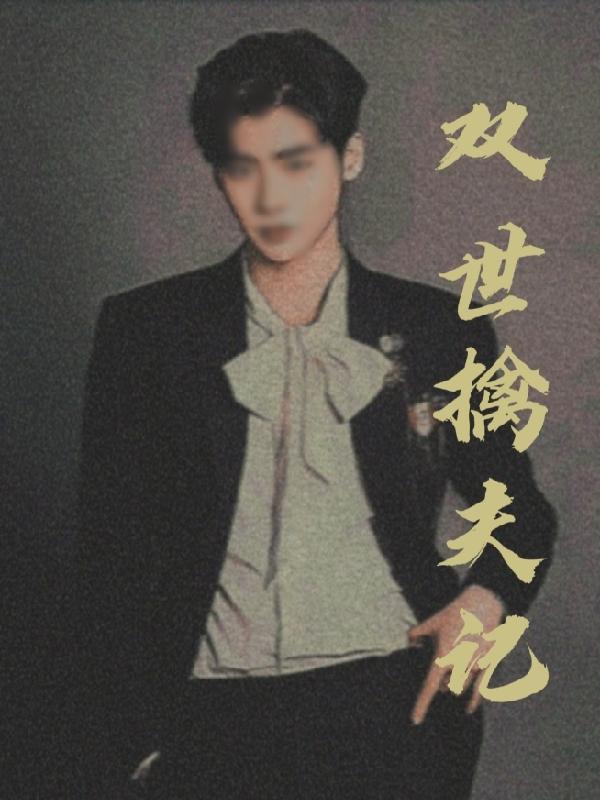风云小说>春山如妆的意思是什么? > 第58章(第1页)
第58章(第1页)
某些时候钟似薇甚至觉得自己在做梦,是一场少女时代延绵过来的美梦。
她和她的春山哥哥,住进了年少时就想要的房子里,过上了曾无数次憧憬过的生活,养猫养狗,他做饭,她帮忙打下手,他加班,她在沙发上看电视,日子宁静而旖旎,幸福甜美。
如果不是愈美莲的到来,钟似薇恐怕都要动摇了。
那天夜里,当纪春山吻着她的额头,轻声而温柔地问她“似薇,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的时候,她真的差一点就答应了。
跟他在一起太好了,是全世界再寻不到的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好,谁不贪恋美好呢?
可是俞美莲出现了。
那个下午,平安和阿呆又打了一架,照例一个找妈妈撒娇,一个找爸爸诉苦,纪春山正试图跟钟似薇讲讲道理:“你也不要这么偏心,刚我看得一清二楚,就是平安先去踩阿呆的饭盆的。”
钟似薇捂住太阳穴:“我有什么办法,你试试它一天到晚在你面前喵喵喵,吵得我脑仁都疼,实在不行你给阿呆多买几顿肉补偿一下吧,哦对,小心点,喂的时候别给平安看到了。”
纪春山无语地摊摊手,低头向阿呆:“你爸尽力了,你爸没用,你爸吵不赢你妈。”
钟似薇被他噗嗤逗笑了,顺手用抱枕砸了他一下:“天天就知道胡说八道,成天你爸你妈的,你是猫还是狗啊?”
“那你说,该叫什么?叫你大姨,叫我大姨丈?乐意了吗?”他不砸她,却也没放过她,伸手就去挠她的腰际。钟似薇最怕痒的,被他挠得上蹿下跳猴儿一样,嘴里不住求饶道:“我错了,你爱叫啥叫啥,叫你爷爷都行。”
“叫我爷爷,那叫你什么?奶奶?”纪春山没有停的意思,两只手追着她挠。钟似薇敌不过,笑得全身瘫软,凑上去勾住他的脖子,贴在他耳边求饶。
她的皮肤这样白皙,鲜嫩的唇就贴在他脖颈侧,吹气如兰,胸腔一下下起伏,贴着他的胸膛,撩出滚烫的情欲来。
纪春山把手放在她的腰际,目光灼热地看向她:“伤好了吗?”
她瞬间红了脸,小声道:“嗯。”
“那可以吗?”
“嗯。”
这一声“嗯”简直要了他的命,全身血液都向一个地方涌,正想就势将她抱进卧室,客厅的电子锁滴地响了。
门开了。
俞美莲出现在门口。
刚还活跃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
钟似薇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这个人给她造成过严重的心理阴影,严重到大脑都还没反应过来,身体就预先做出判断的地步。
而在下意识的退让、害怕过后,一种强烈的屈辱、愤怒迅速地袭来,就像那天在消防间里被捆住双手的屈辱和愤怒。
她的双眸激射出怨恨的火花,几乎是在一瞬间暴起,连半拥着她的纪春山都没反应过来,就见一个身影冲了出去。
钟似薇往俞美莲身上撞过去,疯了一般,双手胡乱拍打,俞美莲下意识想躲,却已结结实实挨了几下,巴掌砸在皮肉上发出闷响。
“你疯了吗?”俞美莲尖声喊道。
“是你害死了妈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还我妈妈!”钟似薇双手掐上俞美莲的脖子,她彻底失去了理智,压抑几年的情绪破了道口子,排山倒海倾泻出来。
她的眼底满是泪水,双目通红着,披散的头发凌乱在脸上,两只手紧紧锁在俞美莲的喉咙处,嘴里发出的声音简直不像喊叫,而像某些野兽失去同伴后的凄厉哀嚎:“妈妈死了!妈妈死了!你为什么要害死我妈妈!”
俞美莲毕竟上了年纪,又完全没有防备,这一下被掐得死死的,眼珠子都险些翻出来,嘴巴半张着艰难地伸出舌头喘气。
纪春山也吓蒙了,一时间呆立原地忘了动弹。
“是你害死了妈妈”,这几个字如惊雷般钻进耳朵,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这几年,关于当年分手的真相,他在心里推导过无数版本,比如纪成锋或俞美莲与钟似薇达成了某种协议,像电视剧演的那样,“给你500万离开我儿子”,又或者是钟似薇提前得纪成锋要立他为接班人,因为不想拖累他而提出分手。
只是无论如何都不敢想田苒的离世会跟俞美莲有什么关系?
他的母亲害死了她的母亲?
纪春山双腿有些发软,脚下像被什么钉住了,根本挪不开步子。
钟似薇还在极怒的情绪中无法平复,她是个擅长内耗的人,二十几年来,从未跟人有过如此激烈的肢体冲突,这一刻是常年累月积攒的隐忍和委屈的迭加,该俞美莲的,不该俞美莲的,通通算在了俞美莲头上。
俞美莲从猝不及防中回过神,终于想起回击,在撒泼打滚这个领域,她显然比钟似薇经验老道,很快便反制成功,不仅挣开了钟似薇箍住喉咙的手,还反身过去薅住她的头发。
“发你娘的羊癫疯,鬼上身了吗?田苒自己短命关我屁事,她的尿毒症是我让得的吗?”
这一幕的视觉冲击实在过于强劲,母亲和前女友扭打成一团。
纪春山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
他一手抻向前推开俞美莲,一手从后面拦腰抱走钟似薇,“似薇,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他说话的时候喉咙很干,底气似乎并不怎么足。
“放开我,纪春山你放开我,她害死了我妈,你知不知道她是杀人凶手!”
钟似薇在他怀里上下乱挣,慌乱中用手肘在纪春山身上撞了好几下,她全然散失理智了,眼泪如雨水般冲刷而下,喉咙里一声声哑叫着:“她是凶手!她是杀人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