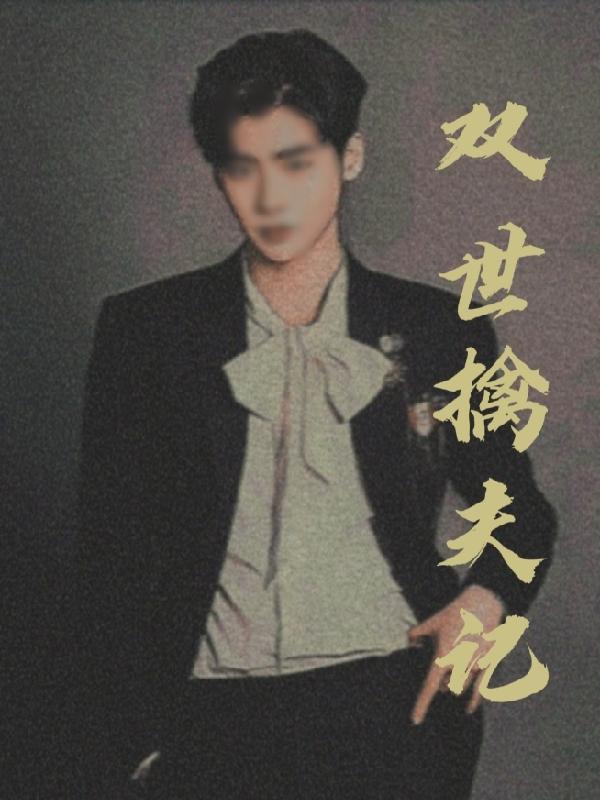风云小说>长恨歌词曲 > 第3章(第1页)
第3章(第1页)
塔提亚应一声,走了。她房在二楼,然她上了楼,却没动作,贴墙而立,屏息凝神,听诗妲库娃摸到地下室去寻烟草。窗外河谷似有阳光醇美只炙烤,使空气温和开绽,几如温柔酷刑,她闭上眼,等着,听诗妲库娃脚步再上,九步后一踉跄,出一声惊呼,又嘟哝两下,坐到沙发上,点了跟烟。屋子里泛着血香;这老太就抽烟一事向来奢靡。塔提亚笑笑,听诗妲库娃叹气,最末沉寂。老贵族抬身回房,步履扣于地上,似与那老旧九阶琴呼应,声响嗡然。门合上了,塔提亚睁眼,摸下楼梯,悄无声息,往地下室走去。她不开火,落地无音,转过储物室,往另一间屋子去,手摸到门把,右手一翻,出片钥匙。她打开门,动作行云流水,如落叶滑进屋内,合门收光,似无事发生。
她点燃灯:塔提亚站在地下书房中,正对面,赫然是座巨大的沙盒,上悬星图海域。白沙如银,取自沃特林海岸,右侧还有只海蜥蜴标本,表皮褪色,几是黑色。她看这颜色,想到乐事,不由笑出声,思绪变换,转瞬又收敛表情,格外寒凉。
她向前走一步,手抚那白沙中,摸到其中散落无数帆船模型,木壳坚硬。她面前正是那张悬在‘君王殿’中的海图,包围兰德克黛因南北,却海色狭隘。最外,一圈天青石般淬炼闪耀的蓝做成火型,上书:‘海渊’。
塔提亚望这使人渺小生畏的海图,目光自右向左,划过那行字:三十二年八月十九日。
她眯起眼。
endofloop
若说诗妲库娃是因青年时投业太甚,全然未管家事而导致这茍延残喘血脉烧百年后终断,却也不准确;她中年时对家族末嗣不可谓不重视。此君少年时和其小叔歌德泼伦美斯明颇不对付,却在青春之走丧,战乱之狂奔中和他冰释前嫌,亦天人两隔,今生永决。失落的爱常是最漫长的爱,无论此侃笑真假,对诗妲库娃言终是有几分真实。歌德泼伦死前交一恋人,乃是东部而来的年轻‘鬣犬’,名系安提庚。说是垂怜也好,造化之残酷也罢,百千曾饮血的女人都不曾唤动那坚硬冰冷的子宫,安提庚却在少年的最末怀上了一个孩子。那时正值‘燃湖’之战前夕,塔提亚和诗妲库娃作南部军队的半吊子统帅,各怀鬼胎,神衰面青,往孛林去,安提庚深夜来寻,面色沉重,默了良久,手抚小腹,道:“我应是怀孕了。”已是近六十年过去,塔提亚仍分毫不差地记得诗妲库娃如如何推椅起身,泪流满面,握住安提庚之手,许久不言。她原先不喜安提庚,却似于那婴孩之苗扎根的瞬间跟安提庚生出了番似姊妹又似长辈的感情。这腹中的孩子使她二人血脉相连,而诗妲库娃再不是光杆将军,‘蓝眼王’家族孤苦伶仃的独苗,而真正是一家之主:她有继承人了。她当即拔剑立誓,无论第二日战场上发生何事,她定护她们母女(她根本没考虑这可能是个男孩的事)周全,全然不管这前半夜她都惶惶不安,内里回荡那些黑红云影。
诗妲库娃确未食言:第二日乃是千年末的化龙之战,吓得肝胆碎裂的士兵数不胜数,她却奋勇作战,杀敌十数,替安提庚挨了三支箭,眼看己方不敌,她全不顾自身安危,只嘱咐安提庚速随塔提亚一同逃离。塔提亚略顿一秒纪念二人同袍一场,接着抓起安提庚便上马飞驰,见诗妲库娃放剑颓坐,在那燃火郁金的树下缓缓闭眼。安提庚于心不忍,塔提亚内心暗叹这便是最后一眼,至于稍后孛林开城,新王大赦,凡不抗不反皆善处,诗妲库娃不但官复原职,财务完好,还在喀朗闵尼斯得了个大官,又是后话了。塔提亚在沃特林海边同安提庚分开,九月后那孩子出生,她自是没看见,同诗妲库娃和安提庚,她那十年,也是面见寥寥。
安提庚在这大宅中生产,诗妲库娃招了四个产婆,六个佣人伺候她出月;她从此卸了军务,和诗妲库娃同住,情谊礼数都似家人。诗妲库娃以待亲姊的礼节待她,余生之中,她对那活在童年故事里的小叔的念想,都给了安提庚。那出生在唐图斯河谷中的女孩也未随蓝眼王家族的中部名,而随安提庚,叫做安多米扬。
安多米扬美斯明在她不到四十年的人生中一直是‘蓝眼王’家族的末裔,却几乎不曾在明尼斯美尔的领地中长留。后称‘沃特林的安多米扬’,这个性古怪航海者,海战家,不愿化龙也不愿出战的大将一度是‘血冠’安伯莱丽雅的左膀右臂。诗妲库娃以她为傲,但在她战败受刑前,她的遗言一句也不曾提及这谆谆盼望,肝肠寸断的姨母。安多米扬被带到羯陀昆定尔城墙上处决,先前显然已受了无数折磨。她身负刑具,跪在城墙上,周遭站满男人,皆面容得意。军队在城下望,迫于‘不龙之约’无以上前,塔提亚见她深吸一口气,满面寒冷,向下吐出遗言。
“操。”那话如此:“真死了。”
说罢刽子手将她拦腰斩断,有龙心,饮龙血者生命力旺盛,她被挂在墙上两日才断气,眼始终望向天边海岸,那蓝眼渐暗,却终不落幕。塔提亚正在下拉着诗妲库娃,听她咆哮撕心裂肺,不让她冲上去给人当靶子。诗妲库娃哭完了这辈子的眼泪,塔提亚看那挂在城墙上的半截身体,嘴角扯出个凄凉的微笑。诗妲库娃一掌挥在她脸上,吼道:“你没有心么?”塔提亚转过脸,眼泪被打出来,也是滑落,默然道:“我还希望没有呢。没有咋还疼,你说是不是?”诗妲库娃遂不言了。她瞧着那半截身体垂头,夕阳染上一头黑发,将它晕成血一般的红色,流光散溢。安多米扬是典型的美斯明家族长相,幼年却生红发,后来才褪了色,但她的生路,始终不褪这血色光辉,无论她如何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