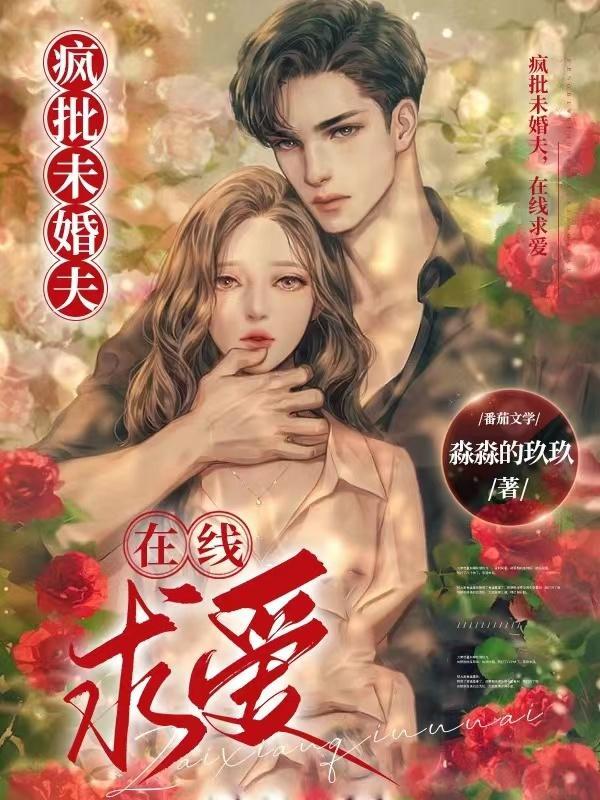风云小说>鹤唳华亭成语 > 第二十九章 歧路之哭(第1页)
第二十九章 歧路之哭(第1页)
·第二十九章·
歧路之哭
定权回到内室,一语不发,于榻上抱膝而坐。不知为何,耳边却一直回响着那只蟋蟀唧唧足足的叫声,时远时近,就是不止不歇。被它聒噪不过,终于握拳向墙上狠狠擂下。他未脱鞋便上床,阿宝已经觉得奇怪,此刻更加心惊,上前捧住他的右手查看,问道:“殿下?”定权甩开她的手,抬头看了她一眼,过了半晌才发问道:“你听到了没有?”阿宝迟疑道:“听到什么?”定权低语道:“你听见他说的话了吗?”阿宝摇头道:“妾没有。”思忖半晌,才又低声加了一句,“妾听见,是许主簿来了。”定权却没有再说话,又埋头沉思,阿宝也只得在一旁静静守候。四下安静得奇异,风不流,鸟不鸣,院内金吾不动,喘息心跳声都如在耳边。她的心头突然狠狠跳了一下,不觉便有了一瞬恍惚,急忙转头,看见定权仍静静坐在自己身旁,才悄悄松了口气。
不知呆坐了多久,直至听到门响,阿宝怔忡抬首,看看门外,轻唤道:“殿下,请用晚膳。”见他置若罔闻,又落地走到他面前,劝道:“殿下今日早膳午膳都没有用好……”话犹未完,定权却突然暴怒道:“滚!”那个送饭的内侍大惊,立刻伏跪于地请罪。阿宝默默上前,轻声对他道:“先放着罢。”
直到月渡东墙,饮食全然冷透,定权始终一口未动
。那内侍来收碗时,见太子不食,只得又报到王慎处。王慎不免又带了一干人赶来问询,却见定权已拉过一床被子,面向墙躺下了,便又向阿宝絮絮唠叨了半晌,询问定权是否当真身体不适,下午可又说过些什么,若是睡起来想进膳,便只管吩咐等语。阿宝终于敷衍到他肯离开,回首看看定权,叹了口气,自己拎了本书倚桌翻看,又看不进去,不过寻个理由,不必尴尬相对而已。
定权却并未能睡得安生,不住辗转反侧。阿宝见他焦躁,几次话到嘴边又压了回去,终于还是忍不住询问道:“殿下,可是身上不适吗?妾服侍殿下宽了衣再睡可好?”定权闻言,终于止住了动作,仍不言语。阿宝方自悔又多事,忽闻他低声道:“阿宝,我觉得有些冷。”
阿宝放下书,起身道:“妾给殿下再添一床被子。”定权不知缘何略感失望,却也没有再多说,见她将自己床上的被褥搬了过来,又轻声道:“我帮殿下暖暖手。”忙点点头,道:“你也坐过来。”待她在自己身边坐下,便将双手伸进了她的两只袖管中。阿宝只觉他的双手冷得如冰一般,不由微微蹙了蹙眉头,问道:“殿下的手足,总是这么易冷吗?”定权点头道:“我从小就有四逆的毛病,太医也说是天生。开过方子,药要经常吃,我没有那个耐性,最后也就算了。”想想又
道,“从前太子妃在的时候,还总记得此事。”
他从未提起过太子妃,阿宝想起蔻珠从前说过的话,轻声道:“妾没有那个福气侍奉过娘娘。”定权淡淡笑了笑道:“是前年的事,太医围了满满一屋,从丑时到酉时,母子两个还是都没有保住。是个小世子,我在外头好像还听见他哭了一声,可别人都说没有,是我听错了。陛下连名字都已经拟好了,就叫萧济。”略略侧了侧身子,捉紧了阿宝的臂膊,道,“太子妃从前也总是这么帮我暖手,要是那个孩子还在,早应该会叫爹爹了。”
阿宝低头看他,他闭着眼睛静静蜷缩在自己身边,周身上下已经没有了丝毫戾气,就好像刚刚束发的少年一般,若不曾相知相处,却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也会有妻有子,为夫为父。她沉默了半晌才劝解道:“殿下还这么青春,谢娘子也是,赵娘子也是,小郡王、小郡主都还会有的。”定权笑道:“我只要太子妃的孩子。我想过了,将来自己也有了孩子,便绝不会教他受半分的委屈。”他口中居然也会说出这样的傻话,阿宝不由愣住了,还没等想好怎么回复,便见一行眼泪已沿着他颧边滑下。
定权亦不想掩饰,阿宝抽不开手,只得默默看着他肩头抽动,半晌方闻他继续说道:“他从来,都没有记得过我的生日。因为逢节,小的时候,先是有家宴,
后来大一点,是有宫宴。王翁一开始哄我,说那就是在给我庆祝生辰。只有舅舅和表哥,他们从来不说重阳,只说初九。有一年初九,是在寝宫外的浴池里跟表哥一起喝酒,喝了一杯就醉了,他把我背上去的。有一年他带我去了京中的瓦肆,可是他害怕舅舅,我害怕陛下,到了地方,我们在外面站了半天,互相抱怨了半天,还是没有进去。更早,是舅舅把我顶在肩膀上,去看灯,吃酥酪,蜜酥食,和我爱吃的东西。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有一颗龋齿。”见阿宝一笑,也淡淡一笑,接着说道:“还有一年,舅舅奉命在京营里。宫宴散了之后,我磨蹭不肯出宫,想见陛下一面。走过去,看见他在教大哥点茶。我在外面,站了一会,看了一会,知道自己进不去,就转身走了。然后,后头有人喊我的乳名,一把把我抱了起来,问我是男子汉,为什么哭?——他是骑了半夜马回来的,见我一面之后,还要再骑半夜马回去。”
定权自嘲笑笑道:“怎么那么傻?根本不用哭的,我还有舅舅。也根本不用羡慕大哥的,我还有舅舅。赵妃她们总在背后说我长得像舅舅,不像陛下。我还想,像舅舅又有什么不好?人家都叫他‘马上潘安’,舅舅又会打仗,书又读得好,我长大了就做他那样的人。有一次,母亲在午睡,我偷偷溜到府门口等舅舅
来。听见外头有马蹄声,我真是高兴,可是最后走进来的却是父亲。我一直害怕他,他总是板着脸,从不对我笑。那天他脸上又黑着,我吓得转身跑开,就听他在后面喝了一声:‘萧定权!’母亲从来不那么叫我,我回过头,才说了一句:‘我不叫萧定权。’他突然就生了气,一把抓起我,掉过手里的马鞭就往我身上乱打。我一面哭,一面喊母亲、喊舅舅,他下手就越重。王常侍劝不过来,只得去将母亲喊了起来。他这才放开了我,也不理睬母亲,一个人甩袖就走了。”
他叙说到此处,忽然笑了,泪水不及收回,便从笑弯的眼角溢了出来,“父亲和我最亲近的,就是那一次,所以我才一直记得。从那以后,舅舅就是来也很少来看我了。可是我知道,他是心疼我的,除了先帝和母亲,这世上就只有他真心疼我。”
阿宝忙牵袖去擦拭他的眼泪,却被他一把推开,良久后才自己匆匆擦了一把脸,道:“先帝、母亲、太子妃、卢先生,他们都不在了。只剩下舅舅一个人了。尊严被践踏,清白被污蔑,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可保护不了他,我生不如死——我宁可这次和二伯一样,死在了这里,也绝不愿意出去看见,绝不愿意看见他……阿宝,你明白吗?”
阿宝摇了摇头,片刻后又点了点头,轻声安慰道:“我明白。”摸了摸他的手
,见已略略温热,这才帮他细细将面上泪痕拭净。定权拉过她的手,抬头问道:“真是齐王叫你来的吗?你真的姓顾吗?你真的叫作阿宝吗?”阿宝脸色一白,方欲回答,便听他喃喃低语道:“不要说出来,说出来,我也许就真成孤家寡人了。”
定权早已疲惫不堪,此刻哭得眼酸,又喝了两口水,过不了多久便沉沉睡去。阿宝却再也难以安心,怕惊醒了他,也不敢动作。及至良久,方想起身时,才发觉自己的袖口已被他抓在了手中。再去摸他的手时,却已再度冰冷如初。她心念一动,才愕然发现自己的一滴眼泪已经落了在他的手背上,便再也按捺不住,紧紧焐住那只手,任由滂沱泪水,恣意夺眶而出。人生于世,能够顺应此心,毫无顾忌地恸哭一场,本来就是奢侈。但是此夜,便随它去罢。
阿宝抬起头,用嘴唇轻轻触了触定权的眉头,安然在他身侧躺了下来。
原本就想错了,所以才一直在为明日打算。直到此刻才明白,只要今晚是天道净土,谁还会怕明朝水火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