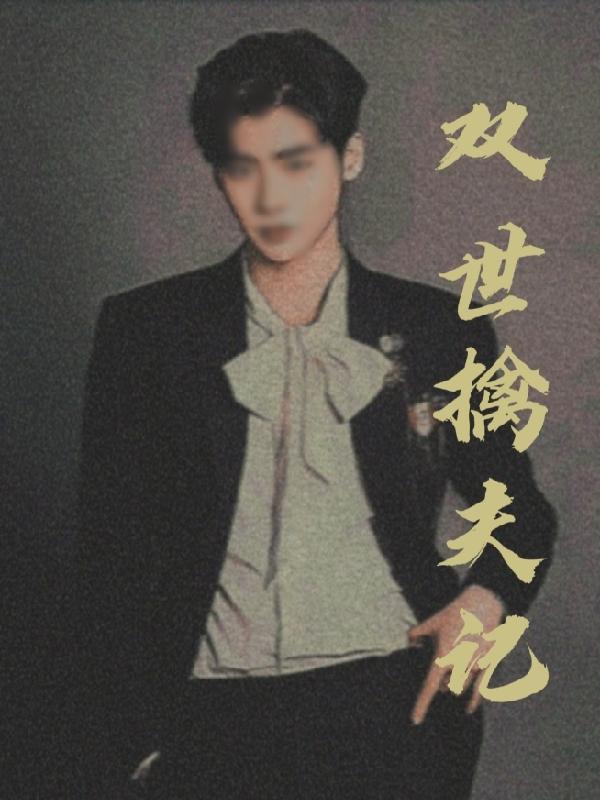风云小说>越轨暗恋by板冬免费阅读 > 窦以晴x秦运(第2页)
窦以晴x秦运(第2页)
“自己撞到墙壁,在这碰瓷儿谁呢。滚开。”熟悉的声音。
“哈?他妈的,你!你别走,来,来,把话说清楚。妈的,你这服务员拉我干嘛?是他撞的我,你他妈倒是拉他啊?”
第一个发现事情的是一位比较矮小的服务员,这醉汉身边还跟着几个同样喝多了的朋友,他只能尽力护着自己老闆,拿起对讲机叫保安:“这位客人,这是我们老闆,他真没撞到您。”
“什么?”醉汉瞪大眼,“是老闆就能欺负人?你还叫人是吧?兄弟们,特么的揍他。”
秦运今晚喝了不少,眼冒金星的,看人都有重影。见对面这架势,知道冲突在所难免了。
衣领被拽起,秦运啧了下,刚想抬脚把人踹开,就听见“啪”地一声。
一个粉色包包迎面砸到对面那个醉汉的脸上。
好丑,好眼熟的包。秦运眯起眼,刚在心裏评价完,就被人拉过去,抱在怀裏。
来人比他矮,又瘦,秦运体型比她要大一倍。对方毫不在意,一手紧紧托着他,从他手臂偏出脑袋去跟那醉汉对骂。
秦运弯腰,脸埋进她单薄的肩膀,嗅着她身上熟悉的香水味,忽然想起前天晚上,有人看不下去,劝他说窦以晴其实也就那样,长得还行但在他们见过的女人裏绝对排不上号,身材高挑但不火辣,不值得他天天在这借酒消愁。
秦运点头同意,说你说得对。几杯下肚后又摇头,说你懂个屁。
窦以晴是他见过最烦,也是最正义的女人。
高中有同学被欺负,第一个站出来帮忙的永远是她,也不管对方是男是女,起身就是干。余斌弘会让她当三年的纪律委员,就是因为只有她胆子大不怕事,谁的名字都敢记。
秦运天天被记名,一直挺讨厌她的。直到高三某一天,他经过老师办公室,听到两个老师在议论他,说他成绩差不上课欺负同学,这种富二代以后到社会肯定是祸害。
秦运根本不在意,这种话对他来说无关痛痒,但在办公室裏帮老师整理作业的窦以晴忽然抬头,冷淡地纠正他们:“老师,秦运从来没有欺负过同学。”
那天以后,秦运再挨她的骂,居然觉得挺开心的,一天不被骂还不自在,他觉得自己可能得了什么精神病,不然怎么会对窦以晴有别的感觉,还每天都很想和她说话?好在很快他们就毕业了。
校庆再见到窦以晴,秦运松一口气——她现在变得好丑,好土,像个大妈,他肯定不会再对她有什么想法。
然后就沦落到今天这一步。
耳边闹闹嚷嚷。那人愣住:“臭娘们,你打我?”
窦以晴闻言举起包又是几下,非常公平地照顾到了每一位醉汉:“滚开,离远点,不然报警了!”
“?是谁该报警啊——”
那几个醉汉反应过来,刚要还手,高大健硕的保安们赶到现场,二话不说上了手,毫不客气地把人拖走了。
事情的过程很短暂,处理也快,经理熟练地遣散掉几个围观的人,赶紧上来想扶人。
窦以晴刚要把他交过去,秦运伸手紧紧把她抱住,牢牢地黏在她身上。
经理认识窦以晴,为难地看她:“这……”
“我扶他上去。”窦以晴说,“给他倒杯蜂蜜水吧,谢谢了。”
到了二楼,窦以晴最爱的那首歌已经唱完了。
窦以晴艰难地把他放到沙发上,刚要起身,又被秦运抱住腰。
他坐在沙发上,脸埋在窦以晴的衣服裏,醉醺醺地问:“窦以晴,你和你前任和好了?”
“关你什么事。”
窦以晴抓住他的手,想把他挪开,又突然顿住。
到了蓝调她就把羽绒服脱了,现在身上只有一件很薄的粗吊带。单薄的衣服此刻被一点点浸湿,她隔着布料,感觉到一片温热。
“窦以晴,你真是个渣女。”秦运闷声说。
窦以晴垂眸:“彼此彼此吧。”
“谁跟你彼此彼此?我从来不和前任搞暧昧,两段我都分得很干净。”秦运更紧地搂住她,像抓着什么救命稻草,“你到底跟他和好没……”
手机铃声打断了秦运的话,窦以晴接起来:“喂?……我没事宝宝,马上回来了。”
腰被松开。秦运撇过脸,不再问了,等她挂了电话,冷冷淡淡地说:“快滚吧,窦以晴。”
一首歌刚结束,蓝调裏灯光大亮。
抱得太久了,秦运前额的碎发都已经翘上了天,脸清晰地暴露在窦以晴眼前,他桃花眼此刻被眼泪染得通红,鼻尖也是,像一隻被扔掉的小狗。
窦以晴不明白,明明都找到新欢了,他为什么还要哭成这样。
她拿起服务员刚送过来的蜂蜜水,想让他先喝一口,有人走上楼来,窦以晴扭头,先看到了对方手裏的稀有皮包包。
“哎?”女人看见只有他们俩人,也愣了一下,“我没打扰你们吧?”
“没有。”窦以晴收回手,“你来喂他吧。”
“我吗?”女人一怔,“为什么?你是她女朋友,还是你喂吧。”
“我就是上来说一下,谢礼我收到了。”女人晃了晃自己手裏的包,对沙发上偏开脸的人说完,又看向窦以晴,“怎么样妹妹?还满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