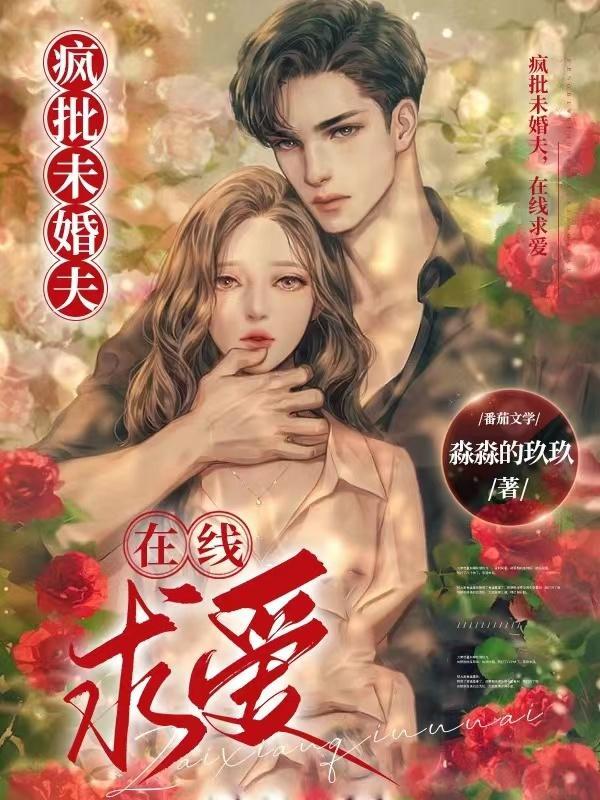风云小说>喜欢了一个有对象的人怎么办 > 第42章(第3页)
第42章(第3页)
已经承认不如人,却仍然不能认命,还是怨恨,还是控制不了地出质问:“凭什么啊?周清。”
被问的人伸手帮他擦掉眼泪,温热的液体源源不断地涌出来,将他的手也打湿了。
……那些温暖的抚慰的话已经说过一万次了。
如果真的有用的话,再说一万次也无妨。
但是那些都拉不住他,像是短效的止痛片,越吃越多,药物成瘾,但下一次作的时候只会更加痛苦,而依赖的药也已经没办法再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
“我不会丢下你的。”周清摸了摸他的头:“你现在赚的钱有一半都归我,离开你再也找不到这样心甘情愿为我花钱的人了,生活质量也会下降,我又不傻。”
许慎抬起眼睛看他。
“而且你还很漂亮。”周清的一只手按着他的肩膀,微微俯下身去,亲了亲那张淡红色的薄唇:“是个很好用的情人。”
明明被人当做工具形容,许慎却觉得整个人都微微热了起来。
“别哭了,真丑。”周清淡淡地说。
他低下头去堵住许慎的嘴,交缠中从嘴角拉出粘腻的银丝。许慎的眼泪止住了,但身体还是下意识地出带有泣音的呻吟,那些声音在亲密的贴合中都逐渐变得暧昧起来。
许慎想要站起来,周清却按住他的肩膀:“就在这里。”
许慎睁大眼睛。
他的背后靠着冰冷的玻璃,春末衣服的布料很薄,全身上下都在烫。周清顺手锁上了门,从许慎身上站起来:“为什么这幅表情?不是每次都要化很久的妆才出门吗?我还以为你很喜欢让人看。”
许慎的脸上烧起一片云霞,他小声道:“不……”
周清解下手表,他脱下外套,剪裁流畅的衬衣勾勒出瘦削的腰。
沉溺其中的似乎只有另一个人,他看上去仍然是清醒而优雅的,衣冠楚楚地像是随时能出去参加工作会议。
“赶飞机很累,我打算十点前睡觉。”他垂着眼说,语气疲惫:“所以我给你3o分钟,就在这里解决。”
“我不会碰你,你自己想办法。”周清的手指和许慎的耳垂一触即分:“做不到的话就说明这是劣等的用具,没用的东西就绑起来算了。”
许慎感到自己浑身的血都在往下走。
“我……”他嚅嗫着说。
“还不开始吗?”周清打断他,他拍了拍许慎的脸,力度不大,羞辱意味更浓:“这会没什么人,万一等会有人突奇想出来散步的话怎么办呢,许影帝?”
被人在这种时候叫这种称呼,许慎的脸上像是火烧火燎一样。他歪了下头,想要将脸贴在周清的手心,尽管那只手刚刚给予了他疼痛,但他就是像有肌肤饥渴症那样想要靠近,但偏偏周清只在最后一下抚摸后就收回了手。他往后退了两步,熟悉的气息重新被涌进来的空气挤占。许慎渴望地看着他:“哥……”
周清摇了摇头:“不行,说了你要靠自己,不要撒娇。”
他就站在那里看着,和早上坐在沙上看着许慎心血来潮做早餐没什么区别。许慎解开自己的领口,露出大片白皙的胸膛,朱红色的两点在爱人的目光之下凸了出来。许慎知道他看到了,他为自己身体的反应感到羞耻,他难为情地低下头,不敢再跟周清对视,然而另一方面,他又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漂亮的,于是又情不自禁地扭动腰肢,想要让他看到自己流畅的肌肉和漂亮的腹肌。这两种念头在他脑海里激烈地冲突着,让他在拿出那根狰狞丑陋的肉棒时,无所适从地掉下眼泪来。
他在周清眼前抚摸自己肿胀紫的阴茎,那东西像是有了自己的想法似的,越是意识到周清在看就越是硬得像石头似的,青筋暴起,顶端吐出来黏黏糊糊的前液。许慎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好看的,但现在这个东西显然和好看搭不上边,快点撸出来就可以把它放回去那他就又是漂亮的完美的了。但该死的,他越是用力越是急切,几乎都要把柔嫩的龟头磨破皮了,那根肉棒就是吐不出东西,还有越来越涨大的趋势。窗外摇晃的树影投到周清身上,提醒着许慎后面随时可能有人经过,随时可能暴露于人的恐惧让他浑身紧绷,但周清看着他
许慎往前伸手,一个踉跄摔在了地上。阴茎和冰冷的大理石地面刮擦的疼痛之后是风暴一样席卷全身的快感。他在那种战栗中缓了片刻,抬起含泪的眼前哀求地看向周清。后者叹了口气,俯下身用手指蹭了蹭许慎的脸颊。许慎想要伸手去抓些什么,却只抓到了周清的腿,戴着假肢的哪一只。
“做不到吗?”周清说:“真笨。”
许慎将头埋在他的手掌里,熟悉的周清的气息将他包裹住。长久的饥渴在这一刻得到了满足,仅仅是一个半拖半抱着的接触就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的下身下意识往前挺,顶到的地方有别于人体的触感,布料之下是冰冷而坚硬的,许慎知道就是那里的机械支撑着周清站起来,原来的部分为了他被丢弃了,现在这个是人造的,假的,劣质的模仿着人体,但却是周清身上真正属于许慎的那一部分。
明明是难过的,是愧疚的,但一想到这肉棒还是涨得痛。
刚刚还怎么都射不出来的阴茎,在抵上那根假肢的时候就开始激动地乱跳。许慎觉得太难为情了,他把头埋在周清怀里,又在快感一波波冲上来的间隙忍不住偷偷从指缝间去看周清的神情。那条腿是没有知觉的,当然,当然,所以周清垂眸看着他,眼中是清醒的,他就像第一次带许慎出去打架之后教他怎么处理伤口那样,那时候他们坐在床上,周清动作很轻地给许慎上碘酒。现在他们都长大了,所以周清半抱半搂着许慎,看着弟弟用自己的假肢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