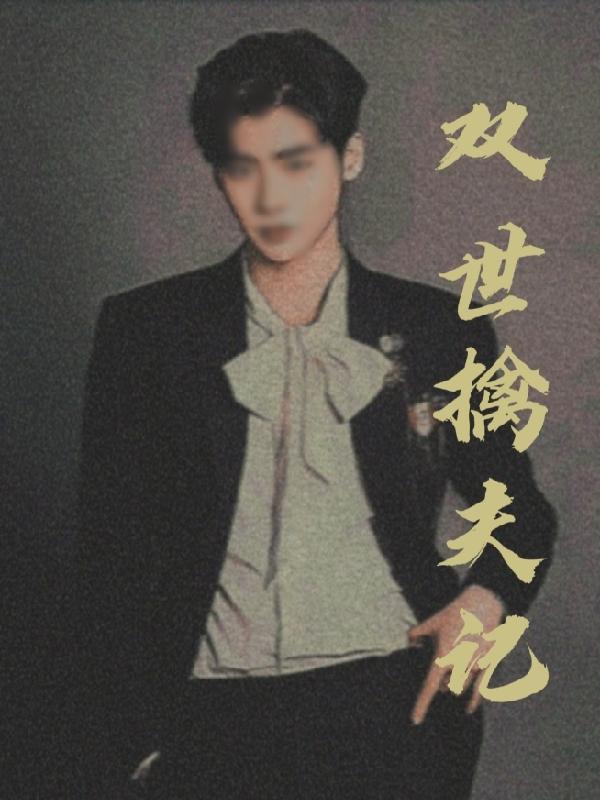风云小说>女扮男装掰弯男主的玄幻 > 第35节(第2页)
第35节(第2页)
宅子乍看极不显眼,就和这风一样,带着市井独有的平易近人,然而风一越过了青瓦白墙,顿时被染上不同于市井的雅致。宅院内里别有洞天,假山池林、亭台楼阁无一处不精致。
僻静小院中,晏三郎隔窗聆听远处的繁华,不由唏嘘。荣华富贵就如灯火时明时暗,自己也是青州的繁华客,一朝落难,照样得藏于暗处。
好在遇到了那位病弱贵公子。
没想到他如此轻易就答应相助,晏三郎不免忐忑,可恩公一派疏离,不似汲汲营营之人,应暂时可信。
总算顺利躲过与害他那人狼狈为奸的官兵入了城,眼下需尽快确信外面那些人中谁人可信,并速速与之联络……
正盘算着,门外有人叩门。
晏三郎应了门,向来从容的人在看到门外少年那刻滞住了。
廊前灯下,立着个霜中竹枝般的清姿,昏黄的灯光削弱了来人周身凛冽的少年英气,只剩伶俜的清冷。
和记忆中的少女有一瞬重叠。
晏三郎定定看着来人。
此时无风,可他眸中映着的灯笼却在微微摇曳,不由自主地,他开了口。
“十……”
“是你的衣服。”
少年听岔了,也像是不喜欢被人打量,眼底显出些不耐烦,面无表情地将手中摆着一叠新衣的漆盘递来。
沉冷的嗓音驱散似曾相识的错觉。
晏三郎眸中微光黯下,恢复从容,得体地接过衣裳:“辛苦竹雪小兄弟走一趟,劳烦代我同恩人致谢。”
谁是你的兄弟……
程令雪不大高兴地腹诽着。
不过看这人的反应,应当是没起疑,她头顶悬着的匕首稍落下。
之前觉得这人应当在下船后就会与她和公子分道扬镳,索性选择躲避,可谁知他阴沟里翻了船,要借公子的地方躲一阵。这时候她就不能只回避了。
还要杜绝一切可能。
所以哪怕不乐意见到他,程令雪还是不得不走一趟。她本想先试探,若是被认出,就用他的行踪和处境威胁。这人是聪明人,定知道怎么最有利。
但他没认出她。
也可能认出了但觉得不重要。
无论如何,有得商量。
程令雪盘算着接下来要怎么说,对面的那个人已先开了口。
“敢问小兄弟一事。”
“问。”
程令雪抬眼,眼底的疏离连暖黄的灯光都照不暖。好在晏三郎常与各种人往来,并不被吓到,只是温和一笑,彬彬有礼道:“敢问小兄弟,恩公素日可有何忌讳?在下叨扰贵府,已是唐突,担心无意间冒犯,惹恩人不悦。”
程令雪负在背后的手愉悦屈起。
她冷然正色道:“我家公子不喜被骗,喜清静,别的没了。”
晏三郎郑重一揖。
“多谢提点,在下必谨记。”
程令雪只淡淡点头,一副不愿搭理任何人的模样,转身离去。
廊下,晏三郎孑然而立,凝着那道清傲挺秀的身影。他记忆中的那个人也很生分,但更偏向怯生生的生分,人亦清瘦伶俜,仿若风一吹就要倒。
想起那个少女,心口一阵钝痛。
或许她已不在了。
。
出了门,程令雪松快不少。
她暗自庆幸,公子这一喜一恶真是妙。那人骗了公子,处境也正危险,听她如此说,应当不会自找麻烦去接近公子。更何况,她离公子比他更近,必要时还能吹吹枕边风……
不对,是耳边风!
想起那日在树丛中的亲密相贴,程令雪一窘,加快了脚下步伐。
刚穿过假山石林,见到个朝她匆匆而来的身影:“竹雪!”
子苓面带感激,小跑着上前:“方才真是多谢你了!我今日也是太不走运,走着走着竟发觉衣袖不知何时给破了个口子,幸好及时察觉,不然被客人和公子看到了,恐怕要惹麻烦。”
程令雪压下内疚,低道:“姐姐不必谢,走几步的事。”
二人说罢,很快分道扬镳,程令雪拐入一墙之隔的主院。
公子正坐在窗前看书。
虽换了个地方,但他往窗边一坐,泠州和青州就没了差别。
这人好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