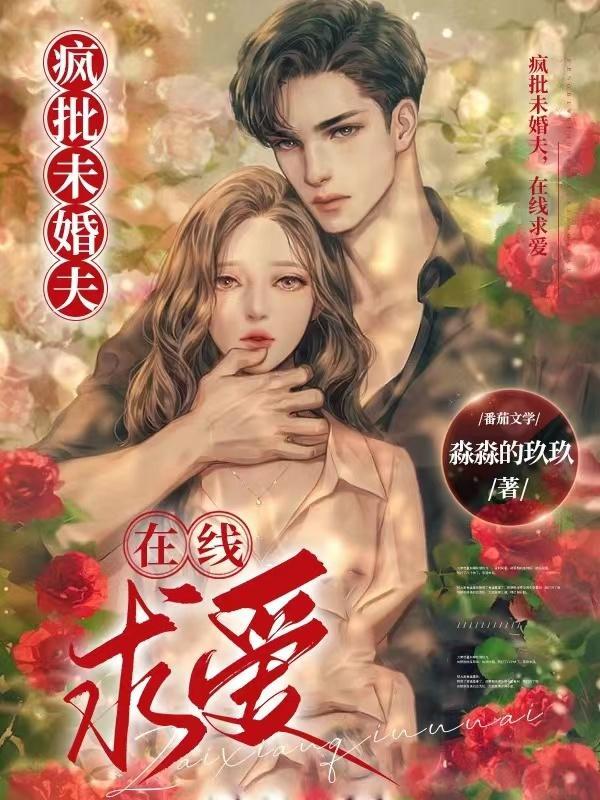风云小说>何不自挂东南枝 爱而不藏自取其亡 天高地阔 欲往观之 > 第92章 土布拉基篇 起步三点头12(第2页)
第92章 土布拉基篇 起步三点头12(第2页)
我说老头,你咋不吱声呢?哑巴了?!
老头的手还在哆嗦,他捂住脸,强忍住的眼泪就从指缝里滑落下来。
【呜呜……我知道,我知道,我应该开口问问,可我太害怕又要失望一场了,我老了,我真的老了……】
【旺……】
我不是很懂。
【没事,她明天还会来的,明天,明天我一定问问她!三十年都等了,这一晚上我还能等不了吗?】
老头阿q似的自言自语,振奋起精神,又开始忙忙碌碌地收拾铺盖卷。
监控那头的工作人员来来回回换了好几个,交接班的时候,始终都会把那张小纸条夹在显眼的位置。
【天冷,他俩爱干净,不用管!】
他叫住准备出去的小王,【刚才那个是下头鹿耳村的老师吧?!就那个破得只剩三间瓦房的那个村小?!】
小王揉揉眼,虽然值夜班他大半时间都是睡过去的,仍然眼睛通红。
【是啊,就是她,还有那个开拖拉机的大学生,我娘说,他们结婚五六年了还没个孩子,指不定谁有点毛病。】
【这话怎么说的?!你娘还认识他们啊?!嘿,跟兄弟说说呗。】
别小看男人的八卦之魂,年纪轻轻搓手嘿嘿笑的样子,颇有几分村口碎嘴大娘的即视感。
【哎呀你不知道,我娘有个老姊妹是鹿耳村的,听说了老多呢,她当年瞧方老师盘正条顺,想把自家光棍了几十年的侄儿介绍给她,被一口回绝,后来没俩月方老师愣是领回来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白面书生回村里,说是扯了证……偏偏她侄儿当初悄悄跑去学校看方老师一眼就上了心,整得那大娘里外不是人,见天儿地一有空就找我娘叨叨方老师两口子的事……我耳朵都听烦了。】
【你说的白面书生,不会就是开拖拉机的那个吧?!】
【可不嘛,你没瞧他天热的时候,瘦得跟排骨精似的,得亏天冷穿得多,这才看起来像个人样儿!】
某只被人背后叫做排骨精的男人稳稳把着方向,用膝盖撞了撞依偎在他身边的女人。
二人对视一眼,温情脉脉,虽然仍有急切,但今天好歹能给孩子们吃一顿热乎的。
车后头用防雨布盖着,绑了一圈又一圈麻绳。
有个袋子搬上车的时候无意中划破了一点儿小口子,颠簸中不时撒出来一点儿。
黄色的,是玉米碜。
两碗就能煮出一大锅玉米碴子粥,黏糊糊的,管饱。
风里已经开始出现小小的雪花,男人心里着急,可脚下油门已经踩到了底。
【方哥,刚才那条狗叫我,我总以为是咱们的大黄回来了,仔细一看,又不是……】
【嗯?!】
【就银行里头,那狗穿一身花布马甲,应该是跟着个流浪汉,他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哦。你不提起大黄,我都快要忘记咱们俩是怎么认识的了。】
——
那是二十五年前,方芳十二岁,刚来初潮。
她一直都知道,现在叫的爸妈不是她真正的爸妈,只是把她当个能干活的丫环一般养着。
只等着她长熟了就给他们智力不全的儿子当媳妇,生孙子。
没人教过她初潮是什么意思。
她蹲在河边用棒槌敲打一家子的衣服,突然流了一裤裆的血,以为自己死期到了,吓得连衣服也顾不得收,哭天抹泪地跑回家。
她妈的反应很平淡,没有安慰,也没有告诉她怎么处理。
【哦,到时间了,可以生娃了。】
方芳到底是上过二年级的人,这句话听懂了。
过了四五天,等她身上干净了,爸妈就把她直接锁进了哥哥的屋子。
窗棂上奢侈地贴了个喜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