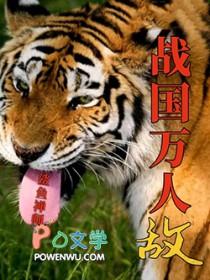风云小说>谁料皇榜中状元伴奏曲 > 第64章(第1页)
第64章(第1页)
房间里一下子亮了许多,他转头一瞧,只见颜昭唯脸色潮红,发丝凌乱,额间垂落的鬓发湿漉漉地粘在白皙俊秀的下颚,顺着修长脖颈蜿蜒而下。
王琅连忙错开眼,却又对上颜昭唯微微泛着泪光、幽怨含情的秀目。
颜昭唯平日对人冷冰冰的,连殷宁皇帝也不例外,偏偏对王琅一副情意绵绵、悲情碎意的模样。
纵是再铁石心肠的人,见到他此刻的眼神,也会软得一塌糊涂。
更何况,王琅并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
幽幽烛火下,颜昭唯盯着王琅深邃的双眼,用仅有王琅听得到的气声,一字一句清晰道:“王琅,我好想你。”
或许是太久未见,或许是王琅心中也一直对颜昭唯放心不下,或许是今夜的烛火幽幽,更或许是颜昭唯此刻实在俊美得叫人惊心动魄,王琅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悸动,一向从容的他,竟乱了气息,胸腔内的那颗心像战场上的号角擂鼓,发出阵阵铮铭,脑海中好似闪过刀光剑影,叫他霎那间失了神。
“王琅,我知道,其实你也喜欢我。”颜昭唯眼神开始迷乱涣散,再次伸手攀上王琅的双肩,“王琅,我,我想……”
王琅却已回神,一把握住他的手,将他扯下来,皱眉道:“你今天都吃过什么?”
颜昭唯眼神迷茫,喘着声音道:“没吃什么。陛下赏我喝了一碗汤,好像是唐贵妃送去的。”
王琅一听,顿时明白怎么回事。
唐俪文在琉璃岛缴获不少稀奇古怪的药方,其中不乏叫人不知不觉意动情迷的药,交给唐贵妃作为后宫争宠手段倒是极有可能。
王琅顿时对殷宁有些腹诽,自己爱妃送的汤,做什么给颜昭唯喝。
“你是从皇宫过来的?”王琅没留意到自己语气中的不满,“怎么在殷宁那待到这么晚?”
颜昭唯似乎已听不分明他的话,闭上眼侧过头,朝他靠过来,想要汲取他身上的凉意。
“陛下叫我留宫中歇息,可是我想见你,就来找你了。”
王琅一听,眉头皱得更深。
这几年,他在外也听到过不少颜昭唯被天子宠幸的谣言,只是他从来不曾信过。
如今看来,说不定殷宁真有些心思。
殷宁年纪比王琅还大些,王琅年幼时,祖父与父亲都回到西北沙场,王琅被祖母送入宫中,与刚登基不久的殷宁坐伴,两人一同学君子六艺,当年宋太傅辞官归隐,太后为殷宁请来白发苍苍的谢太公作为天子之师,那时候殷宁在宫中只有王琅一个朋友,二人也十分亲密,原本谢太公的课,只能殷宁去听,殷宁却执意要王琅陪同,一起学天子之策。
只是,王琅的天赋日益显著,学得比殷宁快,比殷宁精,武学上无论是骑马射箭、还是刀剑枪戟,无一不精。文就更不用说了,书法比起他爷爷还要青出于蓝,诗书经文、琴棋书画更是新手拈来,彷佛这世上就没有什么是他学不会的。
殷宁比起一般人家的孩子,已足够聪慧勤勉,可他学三日的内容,王琅只需小半日便通。殷宁日益勤奋,费好大功夫学会一套精湛剑术,王琅却早已自成一派,悟出一套新的剑法。
长此以往,王琅常常得百官大力夸赞,连甚少夸人、喜欢与王太公互怼的谢太公,言语之间都掩藏不住对他的欣赏之意,殷宁与王琅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便渐渐郁郁不乐。
后来,殷宁亲政,王琅便找了个理由,离开皇宫。
以往,提起殷宁,王琅总是觉得惋惜,昔日挚友,却因身份、天赋之别,渐行渐远。
如今,这份惋惜忽地被颜昭唯淡化,只剩下君臣之别的疏离。
“王琅”,颜昭唯声音中满是焦急,双手从王琅掌中挣开,胡乱地抓着,“别抛下我。”
王琅收敛心神,冷静克制道:“你别乱动,我帮你疏通经脉。你再忍上半个时辰。”
他将颜昭唯放在床上抚正,想坐他身后去点他身上穴位,谁知颜昭唯根本坐不住,也一刻不肯放开手。
王琅见他眼神涣散,脸色从潮红转为苍白,身上不停地颤抖,心下惊诧那汤药的作用竟如此厉害,怕对颜昭唯身体有损,不敢再拖延一刻,情急之下,往日的昵称脱口而出。
“昭昭!别动!”
颜昭唯立刻不动了。
他一语不发,任由王琅摆弄推穴,叫王琅想起当年那个乖巧得不像话的颜昭唯。
迷乱之中,王琅听到颜昭唯发出喃喃之语:
“我已经太久,没听你叫我昭昭了。”
王琅摇扇,天下无双
清晨练剑,是王琅每日卯时必做的事。
他个子极高,身姿挺拔,可是每当他舞起剑来,却只会叫人觉得灵动飘逸,身轻如燕。
剑影绕着他黛青色衣袍游动,与他浑然一体,仿佛他不是在舞剑,而是剑原本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虽王琅舞得举重若轻、赏心悦目,但若是对剑术有所造诣的人,此刻怕是只会震惊于他剑意中的江河湖海,破涛汹涌。
颜昭唯推开窗子,只见庭院里雪白一片,外头不知何时竟下起了雪,大雪弥漫,一片片地似琼花碎玉,叫人如梦如幻。
琼花碎玉中,包裹着一个恣意潇洒的身影,那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招一式都如此赏心悦目,叫他心旷神怡。
虽王琅在外游历了三年,岁月却没能在他身上留下一丝一毫世俗的烟火气,一如当年颜昭唯初次见到他时,那般疏阔洒脱,仪态天成。
颜昭唯第一次看见王琅,是在一个细雨绵绵的阴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