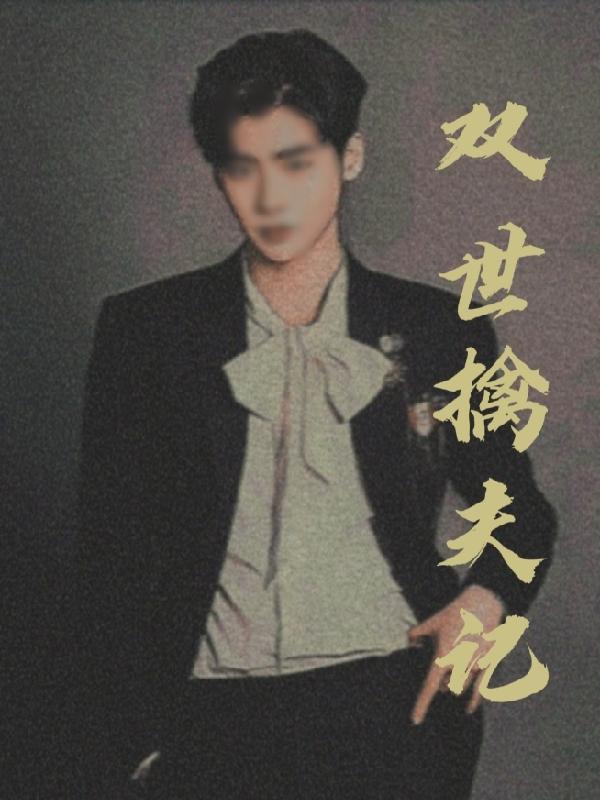风云小说>70年代的图片 > 第30章(第1页)
第30章(第1页)
她走走停停,又想起葛斯熙的伤,刚才还是应该先送他去医院的。
“去哪?”自行车在她身边“吱”一声停下,葛斯熙的脸出现在眼前,“脚受伤了?上来,我送你去医院。”杨廷榕连忙推辞,“我没事,倒是你要去医院检查,毕竟是头部受到撞击。”
“我推你走。”
卫生院的医生拿电筒照了照葛斯熙的瞳孔,只说晚上要是头晕呕吐就再来医院。但杨廷榕脚上的伤口让这位女医生忙活了半天,差不多半瓶双氧水倒在伤口上,总算洗干净创面。杨廷榕眼前金星火星的乱蹿,咬住下唇不吭气,生怕张嘴会痛得喊娘。
葛斯熙在旁边看得直来火,什么医生,连过去的老护士都不如。几年闹下来,有本事的不是靠边站,就是去农场劳动,剩下闹腾得欢的,还有因成分好被提上来的。
好不容易上完药,杨廷榕忍得后槽牙和腿都软了,被葛斯熙扶到外面的长椅上坐着。他又匆匆跑开,说去给她泡杯糖水。杨廷榕想叫他别麻烦,但一时之间嗓子干得说不出话。
她靠在椅背上,起来得早,路上骑车又累,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
直到咣当一声,像是里面医生的器械盘掉在地上,杨廷榕才从梦里醒过来。她眨了几下眼,有数秒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看到葛斯熙才回到现实。她在大庭广众下睡着了!杨廷榕脸顿时火热,悄悄地摸了摸嘴角,幸好没流口水,否则真成笑话了。
“好点没?”葛斯熙摸出两颗水果糖,“小卖部什么也没有。”他剥开一颗,递给杨廷榕,“含上,刚才你可能是低血糖,才会心慌出虚汗。”
他压低声音,凑近她的耳边,“那个不是医生,是屠夫。我们坐在这才多久?她已经掉了两次笔,一次听诊器,一次器械盘。”
杨廷榕也小声说道,“我要回家自己包扎,是你非坚持说医生处理会好些。”
葛斯熙反驳,“我也说我没事,你还坚持让医生帮我先看,…”
话还没说完,新来的病人边骂娘边向外走,杨廷榕下意识地坐正,这动作造成的后果是葛斯熙的嘴唇正好擦过她的面腮。两人同时一愣,片刻后才反应过来。
病人在面前走过,他俩一动也没动,彼此都坐得笔直,隔了半臂的距离。
等人走远了,葛斯熙才转过头,正好又和杨廷榕的视线遇个正着。她像被什么刺着似的,睫毛刷的垂下盖住眼睛。
回去的路上各自心猿意马。
“吃了再回家吧。”葛斯熙自言自语似的说,“都午饭时候了,家里反正也没人。”
“还是得早点回家,要准备晚上的事。”晚上要关上门祭祖,准备工作少不了,杨廷榕看着路边的树说。天空中还飘着雨星,枝头的新芽尚未爆开,但树根旁的野草,已经开出紫色小花,星星点点的占着几分春。
“去元福桥吃碗小馄饨,不费多少时间。”
葛斯熙推着杨廷榕往元福桥去。这里是小吃店集中地,人渐渐多了,有人好奇地打量着他俩,杨廷榕装作不在意,却在人流中看到熟悉的身影。她以为是自己看错,妹妹杨廷薇说过不回来的,怎么这会在城里?而杨廷薇身边那矮个子,是那个姓沈的叫什么的?
他们快走远了!
没等和葛斯熙说起,车身一轻,杨廷榕跳下来,朝左边的巷口跑去。
“薇薇!”
杨廷榕看到,杨廷薇回过头望了她一眼,然后和沈某某手牵手溜得飞快,眨眼不见人影。
怎么回事?杨廷榕满腹疑虑,突然想到姓沈的是工宣队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总能找到他。
葛斯熙追上来,大致也明白了情状,“算了,她不是小孩子了,管得太紧反而伤姐妹感情。”杨廷榕狠狠扫他一眼,却什么都没说,这是杨家的事,她自己想办法解决。她转身朝南面走去,上次依稀听薇薇说过,沈家搬的新地方离原来的家不远,在春晖巷附近。
“她已经是大姑娘,你也不比她大多少,老是管着她会让她反感。”葛斯熙不紧不慢跟在旁边劝道,“你难道盯住她一辈子?要给她自由,碰了壁自然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杨廷榕忍无可忍,“你别跟着我!”
葛斯熙无奈地笑了笑,“别生气,我陪你一起找。”
“不用,谢谢。”
杨廷榕冰冷的脸色和语气,让葛斯熙终于明白一件事,她拒绝他的陪伴,她是认真的。
他努力控制住下落的情绪,平静地说,“那你慢慢走。”
☆、管闲事?
春晖巷、雪霁弄、状元里,杨廷榕在这些街巷度过童年和少年。过去,每户半掩的门后是两进的房屋。慢慢的,住进来的人越来越多,白墙黑瓦渐渐蒙上深深浅浅的灰,而原来的房主已经各散东西。
雨下大了,杨廷榕躲在人家的屋檐下,裤管还是被溅湿了。铅灰色的天空,预示着雨一时半刻不会停。梅城四季分明,春天有丰润的雨水,夏天炎热,秋天晴朗,冬天寒冷。这阵雨过去,路面被冲洗得干干净净,而杨廷榕心里的惊讶与愤怒也退去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担忧,无论怎么样,家里的门总是对妹妹开着的,为什么她要躲在外面?
杨廷榕走到雪霁弄尽头时,几个孩子从拐角处奔过来。跑在最后的那个年纪最小,才两三岁的模样,一头撞在她身上,然后摔在地上。杨廷榕弯身去扶,那个孩子却自己爬了起来,蹲在那拍着地面奶声奶气地叫道,“打!打!”